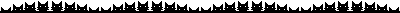廣東雞樅菌的做法(鮮于錦雉膏腴於錦雀腹)
2023-05-03 14:14:04
「老饕驚嘆得未有,異哉此雞是何族?無骨乃有皮,無血乃有肉。鮮于錦雉膏,腴於錦雀腹。只有嬰兒膚比嫩,轉覺婦子乳猶俗。」
——清·趙翼《路南食雞樅》
清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著名史學家,文學家趙翼趕赴緬甸前線戰事。途經雲南之時,見到路旁有賣雞樅的,便買了一些烹食。他吃後驚嘆於其滋味之鮮美絕倫,於是寫下這首一看就不怎麼高明的口水詩。雖有愧於他大文學家的名頭,但詩中那股突如其來的驚喜以及滿滿的誠意仍然撲面而來——無血而有肉,鮮美的能把野禽都比下去,真是活脫脫的一個小鮮肉啊。
「五月端午,雞樅凸土」。這是雲南流傳非常廣的一句俗語。說的就是到了每年農曆的五、六月間,當地最有名氣,也是最名貴的食用菌雞樅就要隨著初夏的雨水大批量的冒出來,開始上市了。說雞樅名貴,是因為它不光野生,還不似其他蘑菇產量那麼高。往往只有在白蟻窩的上面,才有那麼一小簇一小簇的冒出頭來。它太稀少了,出了雲南,在我國的其他地方很難再看到。即便有,要麼質量不佳,要麼就是油浸或者曬乾的加工品了。這是一種帶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食材——從菜譜上看,除了西南雲貴川當地的菜譜中還能看到一些雞樅菜,在別的菜系中也是難覓其蹤跡。
物以稀為貴。一方面它無法人為進行栽培種植,全靠山民一步步的丈量著大山,辛苦萬分的用竹簍背出來。單靠採集本就無法滿足全國吃貨的胃口,更悲催的還是我國大宗出口的商品,每年都能換回不少外匯;另一方面,有白蟻窩才可能有雞樅,白蟻窩的興盛也決定了雞樅的興盛。它極其特殊的生長環境隨著白蟻窩的萎縮也必將越來越少。所以,當山民費勁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找到幾朵的時候,你能說它不難能可貴嗎?
雞樅身世考
雞樅最早的記載於南北朝時期
雞樅因其名貴而天生自帶疏離感,它的名字是如何來的呢?它在美食的歷史中又有什麼樣的經歷呢?首先,這個「樅」字就相當特殊。它最初應寫為「㙡」。相比其他菌類的名稱,它在文獻中的記載非常晚。我國第一本字書,成書於西漢的《說文解字》中根本就未提及它,應是當初人們還未認識到其可食。其後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未曾記載。直到南北朝時期,南梁的顧野王所著的《玉篇》中才第一次提及它為「㙡」,解釋為:「㙡,土菌也」。到了明代,梅膺祚所著的字書《字彙》中,第一次開始將「㙡」與雞聯繫在一起:
「㙡,土菌也。高腳傘頭,俗謂雞㙡,出滇南。」
到了明朝末年張瀾之所著的《不二雜集》中,則第一次提到何謂「㙡」:
「雞㙡,土菌耳。隨土而生,附土而長。故曰㙡。」
即「菌從於土」之意。可惜的是在現在的電腦輸入法中,提土旁加從的「㙡」的簡體字已經無法打出了。人們也就漸漸接受了「樅」字,可實際上,雞樅非木耳,香蕈等需要樹幹作載體的菌類。「樅」實際上是說不通的,也罷,姑且用之吧。
張開傘蓋的雞樅真如鳥飛斂足一般
雞樅的的古稱非常多,這其中也出現了一些謬誤。比如李時珍在《本草綱目》中提到
「南楚人謂雞為㙡。」
筆者不知李時珍當時是如何想的,如若雞即為㙡,㙡即為雞。那雞㙡不就成了「㙡㙡」了嗎?這顯然是毫無道理的,甚至謬誤的有些無釐頭。另在楊慎所著的《升庵集》中,則如此命名雞㙡:
「雲南名佳菌曰雞堫,鳥飛而斂足,菌形如之,故以雞名,有以也。」
如果單從雞㙡的形態,明顯是高腳而立,何為「斂足」之說呢?甚至有些地方,稱呼雞樅菌為「雞腿蘑菇」、「雞腳蘑菇」。怎麼會像老母雞抱窩那樣縮著腳呢?
雞樅的曾用名很多
雞樅菌除「雞㙡」、「雞堫」等名為,在古籍中的名字還有:《七修類稿》中的「雞宗」、《五雜俎》中的「雞踨」、《南苑漫錄》中的「雞㚇」、《永昌府志》中的「雞葼」、《通雅》中的「雞堫」、以及《滇南新語》中的「雞棕」。此外,還有「雞粽」、「雞松」、「雞宋」之類。這其中除開「㙡」,出現頻率最多的就是以「㚇」為主體的代表字了。在《說文解字》中,所謂「㚇」是如此解釋的:
「鳥飛斂足也。註:不能翱翔遠舉,但竦翅上下而已」
原來楊慎的命名出自此處。原來所謂的「斂足」非為「縮腳」,而是指鳥兒無法起飛,上下振翅的形態。如此看來還頗有幾分雞樅菌傘蓋打開之時的神韻呢。
雞樅多生於白蟻巢之上
一個問題解決,接踵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既然鳥飛而斂足,和雞有什麼干係呢?為何不叫鳥樅呢?且雞樅是從地底的白蟻洞中鑽出,有時深達半米。所謂的「凸土」即是如此。故與其叫雞樅,倒不如叫「蟻樅」要合適的多,雞樅畢竟是寄蟻巢而生的,不是嗎?這種說法在一些古籍中也能找到,如郎瑛的《七修類稿》中就曾提到:
「予問之土人,雲生處蟻聚叢之,蓋以味香甜也。予意當作蟻從,非雞宗明矣。」
郎瑛也認為「蟻從」要較「雞從」恰當的多。清代《貴州志》中,也有類似的說法:
「下有蟻若蜂狀,又名蟻奪。因奪起食而,故名。」
在貴州的一些地方,時至今日還有稱其為「白蟻菇」的,且日本也將其稱為「姬白蟻菌」。這也和雞一點關係都無。
雞樅又稱「一窩雞」
筆者曾經帶著疑問請教過雲南的大學同學。他告知我:「雞樅長出來兩天不採的話就會變老,這時候傘蓋就會打開。如果還不採的話隔天傘蓋就會下垂,看起來像母雞的羽毛,所以叫雞樅菌。」我對這個說法是非常不以為意的,雞的羽毛是蓬鬆的,因其表層有油脂,故內部有大量空隙且不易打溼。除非被傾盆大雨淋透變成落湯雞,否則是不可能耷拉下來的。再說形象也不佳,另人胃口大減。而在晚清成書的《閔產錄異》中,福建當地將其成為「雞棲菇」,是因其:
「出土中,以味如雞;以大復小,如雞伏子。」
此種解釋則分外形象,雞樅的確是最大的一個先開傘蓋,庇護著下面簇擁著的一群小的,真就像老母雞抱窩一般。故在雲南當地,採雞樅菌非論只,是論「窩」。有的時候每窩能採幾十隻。有時甚至是三四窩而是分散在不遠的幾塊地上。所以雞樅菌在當地還有個諢名叫「三堆菇」。
除此之外,雞樅菌還有諸如「雞絲菇」、「鬥雞菇」、「逗雞菇」、「鑽子頭」等。有人言它傘蓋頂端如同雞喙,可以拿來逗雞玩,更可以用來作為激怒鬥雞的靶子。至於「鑽子頭」也很好理解,其名生動而有趣,將雞樅菌從土中鑽出的形態和勁頭概括地惟妙惟肖。故說來道去,所謂雞樅菌,還是因為「其味如雞」的緣故吧。
雞樅本身就有雞味,何必燉雞多此一舉
但此類說法也充滿爭議。《七修類稿》中說它:
「而方言謂之雞宗,以其同雞烹食至美之故。」
其認為雞樅菌是因同雞同煮而得名的。筆者則有不同意見——雞樅菌本身就鮮美無可匹敵,且其味出於自身,誰說非要「與雞同烹」才能鮮美呢?宋濂的《遵生八箋》中就提到它是:
「生食作羹,美不可言。」
所以還是李時珍最為實在,爭議不絕的問題到他這裡也就往往戛然而止了。《本草綱目》中總結道:
「雞菌,南人謂為雞㙡,皆言其味似之也。」
在臺灣,雞樅菌又被稱為「雞肉絲菇」,其富含纖維,吃起來倒的確有些像雞胸肉的肉絲。所以所謂的雞樅菌,應該是指味道如雞肉的一種土生可食用真菌無疑了,《本草求原》則叫它「雞樅菜」,就更加貼切了。
雞樅的允悲
雞樅採出後很快就會腐爛
只要是稀罕的,名貴的——在古代都逃不開被皇家列為「貢品」的命運。這其中最有名氣的就是那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的吃荔枝吃上癮的楊貴妃了。其實,雞樅也曾經擔當過這個角色。因其味美絕倫,深得明熹宗朱由校的垂青。為了能吃到新鮮的雞樅菌,每到初夏,他就會欽命驛站快馬加鞭將雞樅送入京師,以解其口腹之慾。可雞樅不比荔枝,它腐敗變質的太快了,且無法像荔枝那樣冷藏運輸。《滇略》中提到它:
「出土一日即宜採,過五日則腐。採後過一日,即香味俱盡。」
《南苑漫錄》中也有:
「出一日採者,朵小而嫩,五六日即爛矣。」
可想而知運雞樅之苦!
增城「荔枝菇」
雲南到北京,時至今日火車都要三十餘小時。當時全靠八百裡加快傳遞,道路又非現在可比,能在一日之內傳遞到京城,那是何等的艱難?據說為了保證雞樅不變質,往往是將整塊蟻巢全部拔起,放入帶孔藤箱中快馬加鞭運抵。送到大內之後,除了皇帝之外也就只有大閹魏忠賢可以分一杯羹,至於後宮嬪妃則是無福消受。當時詩人張紫峴就曾作詩諷刺道:
「翠籠飛擎驛騎遙,中貂分賜笑前朝。 金盤玉筋成何事,只與山廚伴寂寥。」
詩人將雞樅菌諷為楊貴妃的荔枝。也這是直到今天,廣東都仍將雞樅菌稱為「荔枝菌」的由來了。
山民採摘的雞樅轉眼就被官府搶走
如果單獨的一個皇帝享用也就算了,可任何一件上面要辦的事情,傳達到下面都會有一層層的吃拿卡要。正所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加上雲南當地地頭蛇的盤剝和壓迫,採雞樅的山民的日子之艱難可想而知。《南園漫錄》中就曾記載:
「 雞㚇,菌類也,唯永昌所產為美且多。雲南亦有,頗粗。永昌以東至永平縣界尤多,但鎮守索之,動百斤。此物唯六月大雷雨後斯出山中,或在松下,或在林間,不一定也……」
其中有「但鎮守索之,動百斤」則揭露了當地官員的貪婪與蠻橫。何謂「索」?即強取也。鎮守作為當地官階最高的武官,動不動白拿你百斤雞樅簡直就如喝水一般稀鬆平常。只是苦了山民,雷雨之後,山路溼滑,常有失足跌倒滾下山坡的悲劇。統治階級的為了一己之好,哪裡聽得到老百姓的哀嚎苦痛?
雞樅品種繁多,大小不一
筆者在雲南之時,曾和當地老人談起過雞樅。聽老者說雲南的雞樅種類很多,其中小的品種一兩能得六隻;而大的單只就能超一斤。如碰到大雷雨之後,有時採到三四斤重的大雞樅都不稀奇。只是筆者一直心頭都在縈繞一個問題:雞縱是否可以人工培育,像香菇,大紅菇那樣大量生產呢?前些年猴頭,竹蓀都已培植成功且開始上市,這些年就連松茸都已經培植生產,上市售賣了。可如果要想培植雞樅,就必須先營造出蟻巢那樣的生存環境和條件,因為畢竟它和白蟻是共生的。白蟻需要雞樅的地下菌絲來構建巢穴,有時還會將其當成食物;反過來,雞樅菌也需要白蟻巢恆溫恆溼的環境以及白蟻排洩的優質肥料為養分非能茁壯成長。這是何等的奇妙?
至於現在市面上出現的黑皮雞樅,充其量只是一種仿製品。雖摸樣相似,但其香味,鮮味相差甚遠,根本無法和真正的雞樅相提並論。可野生的雞樅幾百一斤,非一般老百姓能吃得起。看來培育真正的雞樅技術還是任重道遠啊。
雞樅入饌
百搭雞樅,即便重味也不在話下
吃過真正的野生的小鮮肉雞樅菌的人估計都能終身懷念其鮮美。作為一種名貴的食用菌,它兼具鮮、香、滑、潤、嫩,脆、甜、韌等特色,是其他菌類所不能匹敵的。這自然會讓人難以割捨。它的做法豐富,幾近「百搭」。從煎炒烹炸到拌烤燜湯無所不能,更可貴的是雞樅大而化之的個性,使它適用於各種味道。不論是清爽淡雅還是麻辣重口,均能體現出雞樅特有的鮮美來。所以雲南當地的大廚根據它這一獨特的個性,炮製出一桌真正的「雞樅宴」。從生煎雞樅、油炸雞樅,到紅燒雞樅、清蒸雞樅,再到椒鹽雞樅、軟熘雞樅……主料皆一種,但烹調出的口味卻是百花齊放,精彩紛呈。就連「麻辣」、「香辣」、「咖喱」等重口味都無法掩蓋雞樅鶴立雞群的鮮味,反而是雞樅將它們的口味烘託的更強烈了。看來雞樅菌非但是個人見人愛的小鮮肉,還是個胸懷寬廣的暖男呢。
雞樅鮮湯
雞樅入饌在袁枚的《隨園食單》中也有所體現。它記載了一個蕪湖的和尚製作「炒雞腿蘑菇」:
「洗淨雞腿蘑菇,去沙加秋油、酒炒熟,盛盤宴客,甚佳」
這種做法極其簡單,洗淨雞樅菌後加醬油,少許黃酒炒熟即可。《素食說略》中則是煨法:
「以滾水淬之,洗去泥沙及粗硬者,與白菜或豆腐同煨,殊有清致。」
一道雞樅燉豆腐白菜的清代「東北菜」。作為素菜雖然寡淡了一點,但是對於那些不願意開葷的人士來說,吃菌就有雞的鮮味,也算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情了。
雙椒炒雞樅
在雲南當地,雞樅菌最常見的吃法就是涼拌和用辣椒清炒了。其做法簡單到有一定烹飪技巧的人士就能完全勝任。因雞樅外皮有些粗硬,故先用粗糙的樹葉擦拭,則可將老皮及泥沙一起擦淨。當然也可直接刮去表皮。將處理乾淨的雞樅菌放入蒸籠中大火蒸十分鐘後取出。再將雞蛋黃三隻,與鹽,糖,胡椒粉,香油攪打均勻,直接澆到蒸好的雞樅上即可。這種做法略顯驚悚,雞樅菌本身就嫩滑,再加上蛋黃的參與,估計會更加爽滑吧。總之未吃過,只能想像得出此菜的口感和滋味。青椒炒雞樅則更加簡單。處理乾淨的雞樅撕成細絲和青椒絲一起下鍋,加鹽,少許料酒炒熟可接出鍋。李時珍說雞樅性平無毒,味甘,有「清心去燥,益胃安神」的作用。因為纖維質比較多,雞樅菌進入腸胃就會加快其蠕動速度,減少食物在腸胃中堆積的時間,從而疏通腸胃。
醬雞樅
雞樅自古保存不易。當古代的勞苦大眾在採集了大量的雞樅後,即吃不了那麼多,又運不出去時,便催生出幾個保存雞樅的辦法來。這其中有將雞樅曬乾後保存的雞樅幹,也有將雞樅用醬醃過的醬雞樅。當然無論如何處理,都會損失一部分雞樅的香氣和鮮味。所以最好的辦法還是將雞樅煉成油。油徹底封死了雞樅鮮味以及香味的散發,用來烹飪和自食,都和鮮雞樅味道無限接近。這種做法至今仍為雲南最常見的保存方法,為大家所喜愛。當然了,古人也流傳下來一些雞樅的加工方法。比如乾隆年間的《滇南新語》中就有:
蕈中有雞棕,大者如捧盒,厚逾口蘑,色黑,鮮妙無比。蒙自縣多產之。土人漬之以鹽蒸存,可耐久,餘滷浮膩,別貯為棕油,或連滷蒸杆(幹)為棕醬,當事群珍之。家常幹之以佐餐。
當地的大戶人家會把雞樅用鹽醃製後蒸熟,也可以做成雞樅醬,為全家所珍愛。
雞樅幹
至於普通老百姓,根本沒有條件做到如此精細。萬曆年間,謝肇淛入雲南擔任布政使司右參政,著有《滇略》,裡面有:
「土人……熬液為油,以待醬豉。」
清代的《滇南雜誌》中則說的非常詳細:
「土人鹽而脯之,經年可食。若熬液為油,以代醬豉,其味尤佳。濃鮮美豔,侵溢喉舌,為滇中佳品。」
清明時期油脂仍然缺乏,普通老百姓只能選擇鹽醃和熬出它的汁液來調味。
李時珍其實還提出過一種炮製雞樅菌的方法:
「雞樅出雲南,生沙地間,丁蕈也。高腳傘頭。土人採烘寄遠,以充方物,點茶烹肉皆宜。氣味皆似香蕈,而不及其風韻也。」
將雞樅直接烘乾,無論泡茶還是燒肉都可以放入一些。這也算是雞樅菌在烹飪技藝上的一個特點。當然現在最常見的還是油雞樅,用上等的菜油或者花生油泡製,質量自然今非昔比。既可以長期保存,又可以遠程運輸,在一定時間內食用,香味也不至於揮發,可以算是最好的雞樅加工方法。只是價格略貴,老百姓無法常食,說到底,還是快一點攻克雞樅菌的人工培植吧。
尾聲
為了採摘雞樅菌,人們必須保存白蟻巢。可保存了白蟻巢,則會帶來極大的危害。白蟻是重大的工程隱患之一,堪稱破壞木質工程的黑惡勢力,其危害程度還要強過老鼠。葛洪在《抱樸子》的提到的「千丈之彼,潰於一蟻之穴」振聾發聵,指的就是白蟻。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白蟻和雞樅一害一利,該如何取捨呢?是為了消滅白蟻而戒掉雞樅的美味,還是為了雞樅而姑息養奸,讓白蟻做大呢?「生存,還是毀滅」,這真是個難以兩全的問題。
從人工繁育的角度上來看,估計還是需要保存白蟻,才有可能尋找出大量培植雞樅的方法。可是為了雞樅而去繁育白蟻,那就是堅決擯棄的觀點了。有可能你的雞樅還沒培育成功,整棟房子都已經這夥黑惡勢力掏空。這樣看來,似乎雞樅菌的大量生產理想前方橫亙著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
不過,筆者還是樂觀的堅信這一天終會到來。我們的玉兔都登上了月亮,我們有了自己的手機晶片,有了自己的大型精密機械。無論再難也能想辦法實現,連區區的不需要白蟻就能長出來的雞樅都研究不出來?這怎麼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