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從來不會讓你失望(別看電影了不適合你)
2023-06-25 07:09:13 3
電影從來不會讓你失望?Start From Here舌尖抵上顎,清晰地發出——洛,舌在唇齒之間——麗,最後輕輕貼在牙齒上——塔這是我喜歡的一句開頭,還有普魯斯特的,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時候,蠟燭才滅,我的眼皮兒隨即合上,都來不及咕噥一句「我要睡著了」半小時之後,我才想到應該睡覺這一想,我反倒清醒過來至於為什麼喜歡,也許是人們對於切身體會的事情都會銘記吧,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於電影從來不會讓你失望?以下內容希望對你有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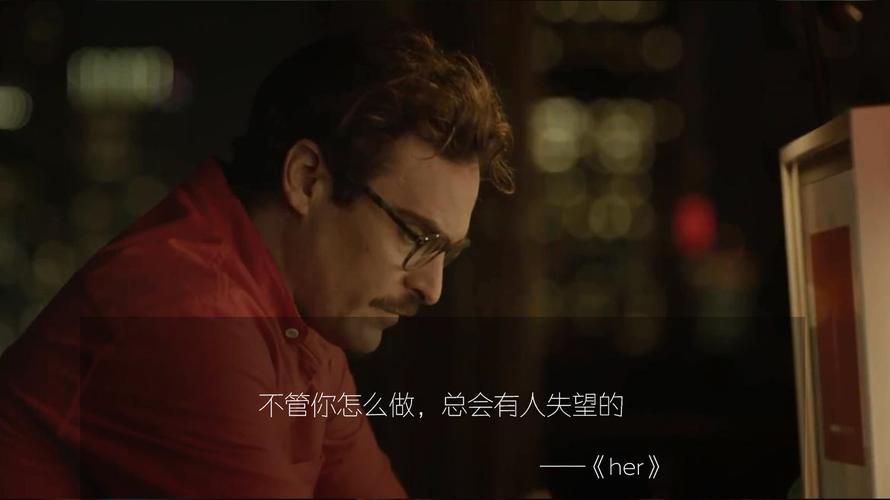
電影從來不會讓你失望
Start From Here
舌尖抵上顎,清晰地發出——洛,舌在唇齒之間——麗,最後輕輕貼在牙齒上——塔。這是我喜歡的一句開頭,還有普魯斯特的,在很長一段時期裡,我都是早早就躺下了。有時候,蠟燭才滅,我的眼皮兒隨即合上,都來不及咕噥一句「我要睡著了」。半小時之後,我才想到應該睡覺。這一想,我反倒清醒過來。至於為什麼喜歡,也許是人們對於切身體會的事情都會銘記吧。
很早就有想法把那些書的開頭做一分析成文,又怕陷入八大組合段似的尷尬,於是罷了。電影開頭亦是如此。
《2001太空漫遊》開場鏡頭便是——月球緩緩落下,地球緩緩上升,在更遠的地方,太陽在地球上方升起。背景音配施特勞斯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真是再貼切不過了,這月落日升,不正好詮釋了尼採的從猿到人再到超人理論麼。
再有趣點的,便是李安的《喜宴》了,開頭的活塞運動,一上來就讓人不覺羞紅了臉,即便《金瓶梅》也是先勸誡一下世人,才開始清河縣西門大官人的。
至於《盜夢空間》,似乎結尾旋轉的陀螺更為扣人心弦,就如同《寂靜嶺》小女孩最後的那張臉,預示著他們似乎永遠停留在這個表世界,無法再與裡世界的男主重逢了。這也是《盜夢空間》一直在闡述的夢境和真實,且拋開夢的層疊數到底是四層還是六層,單就真實而言,本來就是沒有絕對的。我拿著蘋果站在你面前,你告訴我手裡拿的是什麼,你會毫不猶豫地告訴我是蘋果,可我站在500米外,你再告訴我手裡拿的是什麼?所以,我更偏向於一元論,無論夢境重疊幾層,他們都是存在的,存在即合理,不是麼?就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你更願意相信哪個故事一樣,問題在於你的選擇,而不是故事本身,故事本身的真假已然不重要了,縱然香蕉不能漂浮起來,猩猩就是母親,那躺著的海島即女人體。影評原本就是過度解讀。就像《禁閉島》中的男人,到底孰是孰非,同一個事件,兩種故事存在,這便是觀點的差異。
今天我們要探討的,是諸如這一類影片的觀賞性,與之相較的是剛映的《私人定製》,且不論馮小剛把《甲方乙方》的老梗拿來賣是否欠妥,單就此片的存在意義就是值得商榷的。觀影過程似乎在侮辱觀眾的智商。
當然,不是所有影片就得如《恐怖遊輪》一樣需要人動腦就是好的,但是至少觀眾可以回味女主存在哪四個交叉點,是怎樣完成這一幕幕追殺的,乃至最後答案揭曉時男孩在車中聽到的音樂與遊輪中同曲,男孩以及母親到底在什麼時候死的,似乎都值得回味,甚至其存在比前段時間剛上映的《無人區》更為有意義,隨著全國電影市場出現井噴,熒幕數量日益增多,而大部分人坐在電影院看電影,卻越發感到枯燥。為了讓觀眾值回票錢,《驚天魔盜團》這樣的片子日後肯定會越來越多,因而它對導演的專業素質要求更高。正如《時間簡史》暢銷的英國,《盜夢空間》的導演諾蘭對於幾何,對於線性的理解,讓這部電影熠熠生輝,而非淪為平庸。
當然值得注意的誤區也正是當今中國恐怖片的誤區——當心開頭餅畫得太大,於是團不了圓,如《樓》,《女蛹》,《孤島驚魂1.2》等等。這樣的片子更像是披著恐怖外衣的搞笑片,片場總會發來笑聲,而對於《招魂》這樣對前輩《驅魔人》致敬的影片似乎也提不起觀眾多大的興趣,歸根結底,現在的電影已然不是技術(be honest,看《地心引力》的時候,我都快睡著了)和特效(近年來的3D電影,除了像《環太平洋》這樣必須依靠技術支持的電影,像《西遊降魔3D》等純粹是增加票房的利器啊)。當於正又開始翻拍《神鵰俠侶》時,觀眾對於翻拍,必將到達一個忍耐值,所以,當前電影市場尋找的出路,便是創新,當然,不是像《飛虎出徵》一樣流於惡俗,而是行之有效的創新。
如將3D技術運用到《肉蒲團》,雖然想法是好的,可影片劇情不敢恭維,太過誇張,於是沒有了誘惑,說到這裡,隨著影片審查制度趨於完善,分級制度也是呼之欲出,將3D技術運用到情色電影中去,必然成為一大趨勢,如卡梅隆所言,中國為什麼刪減掉jack給rose畫像那段,是怕後排觀眾相去摸而打到前排觀眾的頭。
為什麼說中國電影將3D技術運用到情色元素大有可為呢?援引李安的《喜宴》來分析,電影中最為奪人眼球的便是那場婚禮鬧劇,這也是五千年中華民族處在一個不尷不尬的契合點上爆發出來的東西。自古以來,中國把性作為必須遮掩起來的,不可見人的東西,然而隨著西方文化和改革開放,性解放在中國其實悄然蔚然成風,可一直被壓抑,不可示人的性,卻在婚禮及婚後卻被認為是極大的,正如前段時間熱播的《咱們結婚吧》,有網友調侃還不如改名《咱們生孩子吧》就是這樣,行周公之禮,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卻與之前一直壓抑禁忌的性產生矛盾,而這一矛盾的切合點便是婚禮鬧洞房,於是全國各地都爆發出鬧洞房的伴郎將新娘伴娘扒光。。。的新聞層出不窮。想想或覺可笑,其實深究便是長期以來被壓抑到現在被搬上檯面來講的一種爆發,這種爆發也將體現在未來中國電影的表現上。
接著是恐怖驚悚元素,同樣的,中國內斂的文化造就了一系列心理恐怖電影《見鬼》等,當然不乏《餃子》這樣濫竽充數的,因為文化差異,倘若搖拍中國元素的恐怖片如《電鋸驚魂》《死神來了》等只會像《維多利亞一號》一樣落得三級片的下場,又有高明的如;林正英的殭屍,存在感又過於強,於是逐漸消逝。而今,又可將3D運用到恐怖電影中,便更可使觀眾身臨其境,於是有了《貞子》的翻拍,然而,既然是翻拍,於是又落得跟《泰坦尼克》《侏羅紀公園》一樣的窘境,論題材,確實3D更好,可既然是翻拍,便沒了新鮮感,能吸引眼球的便只有懷舊,電影發展不可能只靠懷舊,電視也是一樣的,雖然靠購買韓國版權的《爸爸去哪兒》爆紅,可不成功的也比比皆是,湖北衛視的《我的中國心》,四川衛視的《兩天一夜》,無論電影還是電視,都亟待創新。
創新分為,一。內容的創新,如《咱們結婚吧》這樣不落俗套,俏皮的臺詞等。而不是一味地翻拍包括楊冪要翻拍的《緋聞女孩》
二。形式的創新,如郭敬明要將成名作《幻城》拍成電影,其實根據文學作品改編城電影早已有之,可之前的改編夠太過於嚴肅,典型就是陳凱歌,還有張藝謀,嚴歌苓的本子似乎在當下電影市場煥發不了多少生機,可總有人願意去碰壁,這也是我一直匪夷所思的,包括《危險關係》再到《金陵十三釵》。當然也有例外,如李安編自張愛玲的《色戒》。
還有一種形式的創新,便是講故事方式的改編,《禁閉島》《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都是這樣,讓電影不再拘泥於故事本身,而是給觀眾無限的遐想和思考空間,這類電影早在《穆赫蘭道》之前就已經出現過,可當時的人們進電影院只是為了消遣娛樂,不會煞費心思思考電影背後的故事,可現在的觀眾似乎更偏向於買帳這類電影,正如同流行的定義一樣,這類高智商電影正悄然流行。
索多瑪一百二十天
很長時間以來,這部位列世界十大禁片之首的電影,似乎難登大雅之堂,更不會有過多的專業影評輔以贅述,然而,這部電影實則導演帕索尼裡的炫技之作,更成為cult片的一面旗幟.對帕索尼裡來說,其意義不亞於陳凱歌的.
帕索裡尼,這位死亡模仿藝術者,後新現實主義時代導演,毀譽參半的大師,卻死在萬聖節和萬靈節之間的那個寒冷的夜晚。帕索尼裡的猝然暴斃,震動了歐洲文藝界,教士們在他屍骨末寒時便開始驅除他的邪惡魂靈,而他的崇拜者們則尊奉他為「聖—皮埃爾·保羅」。
而帕索裡尼留下的,就是最為警世駭俗,也是自己導演生涯的最後一部電影,電影改編自薩德的同名小說,導演將故事地點從瑞士搬到二戰末期臭名昭著的薩羅共和國。
電影的段落構成,分四個部分,分別借用了但丁《神曲》中的「地獄之門」、「變態地獄」、「糞尿地獄」和「血的地獄」四章,這秉承了帕索裡尼作品一貫的古典風格,寓意旨在反法西斯.其實帕索尼裡最早,是在在文壇上以詩人成名,並且經常向古典名著取材,比如《俄狄普斯王》《十日談》《一千零一夜》等,
而帕索尼裡的死,也是極具戲劇性,如同埃克蘇佩裡,在寫完後,死在了沙漠裡,帕索尼裡則死在萬聖節呵萬靈節之間的夜晚。如此看來,現在好萊塢特立獨行的波蘭斯基,相比於帕索尼裡來說,似乎有點小兒科了.
帕索裡尼利用薩德的描寫與當時政治相結合,對代表統治階級的四種權勢神權、法權、政權和封建勢力進行無情的嘲諷和揭露。電影結構形式的完整和思想內涵深邃,引起西方電影界的重視和爭議,也反映出導演本人世界觀和方法論的複雜性。因為宗教本來就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就像即使瑪麗蓮曼森信奉的是撒旦教,也並不影響他搖滾醉人的魅力.
對的爭議,持續至今,有許多人讚賞影片勇敢無懼的直接,也有其他人認為導演過度自負,時至今日,這部電影在許多國家,仍然無法播映或發行。
關於電影被禁,除去影片內容的不適,主要在於薩德故事本身,對現代權力,個人的關係和消費性社會的隱喻。這部巨著,是薩德被關押在巴士底獄期間,在一個類似於衛生間捲筒紙上寫下的,一個封閉的、道德無涉的、只為作者本人存在的自洽世界.無論是篇幅還是內容, 都無愧於巨著的稱號。
正如巴塔耶所言------如果一個人真的想理解一個概念,他就必須在這種概念中非知性地活過,帕索尼裡死了,也留下了諸多疑點,迄今仍是神秘的謎團,有人猜測這是有計劃的政治暗殺,有人哀嘆這是一場藝術的殉難,文化的儀式。
如若沒有經歷二戰歷史性的地震、沒有在馬克思主義和弗洛伊德思想中浸染過,帕索裡尼斷然不會拍出這樣一部驚世駭俗的電影, 是帕索尼裡繼"生命三部曲"之後,留下的一曲絕響.
薩德小說的核心是快感,而帕索裡尼卻回溯到法西斯時代,讓成為歷史批判論文,更將矛頭直接對準了每位觀眾。並且顯示了高度的自反性,一如卡爾維諾所言:「薩德在我們體內。」
《伊莎貝拉》
彭浩翔說這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喜歡的一部,我感覺亦然。可能大部分熟悉他的人都鍾情於他一貫的黑色幽默和惡趣味,從《買兇拍人》到《大丈夫》從《公主復仇記》到《AV》,「怪雞」的風格在那些結構精妙的故事和忽冷忽熱的幽默中畢露無遺。但這僅僅是他的一面而已,喜歡村上春樹和米蘭·昆德拉的他骨子裡其實有種很深沉的浪漫,而這種浪漫凝結起來就變成了《伊莎貝拉》。這種浪漫乍一望去和王家衛頗為神似,但細細揣摩就會發現內在其實相差甚遠。王家衛極端風格化的鏡頭語言與他凌亂而抽象的人物和故事是相互照應的,如果之前沒經歷過幾部錘鍊的話你往往會因為無法進入而感覺不知所云。彭浩翔在這部作品中影像風格的轉變是顯而易見的,但這種看似流光溢彩的風格並非刻意而為之,完全是為了把這個略帶憂傷的故事講述的更為貼切。換句話說,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樣,一切仍然是為了一個好故事服務,只不過這次換了種講法:不再嬉皮笑臉,而是略帶深情。
《伊莎貝拉》的背景設定在回歸之前的澳門,可能是為了讓觀眾最大程度的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人物角色和澳門的街景上,彭浩翔好像故意清空了城市。在他的鏡頭下,古老破舊的街道上除了男女主角之外,幾乎沒有其他的人。張碧欣和馬振成漫步在街頭時,就好像一座遺失千年的古城中突然闖入了兩個塵世間的人來。而在他們漫遊的軌跡下,你會隨之領略它的點點滴滴。
我對有如此敏感和責任的導演向來是心懷崇敬的,不管這種驅動力源自內心的何處,他們最終將鏡頭對準了那些即將逝去的現實景象和背後的文化情懷,這種作為都是值得讚揚的。
澳門畢竟是被葡國統治了百年的地方,回歸大陸意味著有些延續百年的東西即將慢慢散去,有些可能會永遠消失,它們是什麼具體說起來可能沒人能分條縷析說的清楚。但在他的鏡頭之下我們可以跨越時間的鴻溝去感受,可能僅僅是一條破舊的街道,也可能是一兩個人的命運。我們循跡而往那些地方可能早已物是人非;我們駐足於光影之中時又真切地置身其中。在這一刻,時間變得永恆。
其實有如此情懷和念想的導演並非彭浩翔一人。杜棋峰在《文雀》裡同樣把鏡頭對準了香港即將消失的那些地方,只是個人感覺他玩性太重,讓幾個扒手的故事吸引了幾乎所有的目光,隱藏在他們背後的那些曾經在不經意間就被忽略了。不能不說的還有賈樟柯,他其實一直在安靜的記錄這個時代,這個風起雲湧日新月異以至於人們無暇駐足思考的時代。《小武》《任逍遙》和《站臺》可能離我們太遠,因為那不是我們的青春。但《三峽好人》和《二十四城記》則是一種擔當,他用一種靜默的力量告訴我們,這個在衝突中緩慢行進的國家裡,有多少人和事不應該遺忘,但事實上我們卻毫無知覺。
《伊莎貝拉》中有很多耐人尋味的空鏡,或者是天空浮雲或者是青郊草地,昏黃的街道盡頭才有一兩個寂寥的人,與此同時,金培達的音樂總是在最合適的時候響起,渾然天成。這是我第一次靜下心來品到了這些空鏡的韻味,或許是我和導演的口味太過相近,我很明白他想要表達的是一種什麼樣的心境,我很感謝他如此完美的展現了出來.
彭浩翔的女主角都很幸運,因為他最善於在電影中展現她們最美的一面,而且用恰到好處的方式把它放大至賞心悅目。比如《公主復仇記》裡的鐘欣桐,比如《出埃及記》裡的劉心悠,幾乎都是讓人過目不忘的角色,基本都是她們演藝生涯中最好的表演。即便如此,梁珞施在《伊莎貝拉》裡的表演還是太過驚豔,我第一次看時還不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看完後驚呼香港什麼時候蹦出這樣一個演員。
她飾演的那個失去母親追尋父親的女孩,很堅強但也很脆弱。她在二者之間不斷游離,時而裝作大人,時而變回孩子,我想每個男人對這樣的人都忍不住要疼愛吧。
她在小飯館裡模仿梅豔芳《夢伴》的一個場景已無需多言,神來之筆往往就是這樣的一兩個細節。
其實今年聞聽她早早嫁為人婦的消息時我還莫名失落,一入深閨之後再次回到大銀幕上的機會肯定少之又少了。雖然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方式,但私心還是希望有這般潛力的她,能在她最好的時刻,有更多的角色永遠的留在銀幕上,繼而成為永恆。
雖然我們永遠無法打敗時間,卻總是希望美好能以某種方式實現永遠。
《你那邊幾點》
援引蔡明亮的《你那邊幾點》,我們不禁想問,楊德昌被延長了三倍的生命,現在是幾點?在《一一》裡,我們見識到楊德昌作為一名忠實的記錄者所還原生活的真實,那是一種流動著的生命,平凡而具原始的張力,並將於長鏡頭的麾下,納入時代的洪荒。成為一個家庭,一個時代的烙印而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各種人物的命運在此娓娓敘來,像片頭的那聲嬰兒的啼哭,預示著生命伊始便是以這樣猝不及防的姿態到來,各種人物也因一場婚禮而交匯到一起,而後又沿著各自的生活軌跡,徐徐展開一幅幅社會風情畫,沒有做作抑或雕飾之嫌,有的只是回歸生活最真實面的無奈,喟嘆,思考和探索。就想小孩一直想通過照片,讓每個人看到自己的後腦勺,這是一種生命最原始的求知慾和獵奇心態,而隨著光影荏苒,人們從什麼時候開始忘了,應該是從不經意間放到陽臺上的垃圾袋,闊別多年的初戀,朋友間的起落,於是我們開始追逐,追逐一些當初並不想要的東西,卻忘了我們來時的路上,有我們依戀的風景。
因為回顧走過的路,有太多的遺憾,於是開始剖析和反思,於是,一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映入我們眼帘,整部影片充斥著荷爾蒙的味道,那麼肆意,像彭浩翔在《伊莎貝拉》裡,借餘文樂的嘴,對梁洛施說出看似輕佻,實則擺脫了桎梏,而洋溢著自由青春的那句耳語——如果我是你,我會選擇放縱一晚!這也是張內鹹在《草莓百分百》裡竭力想營造的一種青春。青春是什麼,青春是暴走的性慾,青春是勃起的生殖器。青春是朦朧的,像巖井俊二《關於莉莉周的一切》,都是那麼突兀,那麼不知所措。青春又是一直《在路上》的,像楊德昌塑造的那個拿著照相機的小孩,總在尋求問題的答案,於是我們不經意發現,曾經我們以為喪失的答案,原來不經意間就可以找到,像魯迅取名《朝花夕拾》一樣,一樣的困惑,卻又不一樣的態度,於是得到的,是不一樣的人生,而人生又是什麼?是在《平凡的世界》裡,過上孫少安的生活,娶妻生子,衣能遮體,食能果腹便是一種幸福。或者,我們可以選擇孫少平的人生軌跡,並沿著這條充斥著荷爾蒙,洋溢著青春的路一直走下去,會有荊棘坎坷,會有不如意,但是這不正是青春的含義麼?於是回到楊德昌為我們呈現的那副遙遠的畫面,一個庸懶的午後,淋漓的鮮血將我們的血脈逼至膨脹,這到底是犯罪還是一場青春的祭奠?沒人知道,答案在觀影人的心中。
A Brighter Summer Day,多麼像姜文《陽光燦爛的日子》,卻生生譜寫出人物的悲劇,現實的悲哀,時代的無奈。那場殺人的場景,就像《紅高粱》裡野合的那段場景,分明是神聖猶如儀式般,衝擊著觀眾的心靈,這也是一場關於青春的儀式,無關乎對錯是非,只是靜靜地記錄下這延長三倍的生命中,驚鴻一瞥。
做生活忠實的記錄者,用虔誠的長鏡頭記錄下洗淨鉛華的生活,這是侯孝賢的長鏡頭之美,有時甚至不覺偏激許多,然而楊德昌則是更忠於生活的,不免要比侯孝賢更是將導演的意識形態完全消融在緩緩流淌的鏡頭之中,我們會驚異於沒有雕琢的原生態美感,這是生活賦予我們的,也是楊德昌留下的。
仔細把玩楊德昌電影裡的人物與情節,除去是忠於現實的展現,更是對當時社會問題的一種話語權,這種話語權不過是隱含在電影後面的一種潛意識的表先,含而不露。當然,這被過度解讀的楊德昌電影可能會被抬上莫名的高度以致難以企及電影本身而更多的是注意到電影延展開來的一系列話題,而這些不正是電影的魅力麼?落一葉而知秋,窺一斑而覽全豹,只有將電影的時代背景聯繫導演當時的創作語境,才能更好地理解楊德昌電影之於臺灣電影,之於世界電影的價值所在,而不能僅僅湮沒在浩蕩的電影本身中,而更應該注重電影之外帶給我們的思考。
電影是一門休克的藝術,現實的漸近線,心裡記憶的兩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