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這電影才知道黃渤為什麼火(這事不怪黃渤但也恰恰證明)
2023-06-19 03:51:15
電影圈「勢力版圖」變化,既悄無聲息,又無比赤裸。
《獨行月球》上映短短幾天票房破15億,首日93.4%的票房佔比,還破了影史紀錄。
沈騰的票房號召力再次被證明。

相比之下,另一位「百億影帝」就有些落寞了。
他就是黃渤。
如果不是《外太空的莫扎特》上映,皮哥都快忘了中國影壇還有這麼一位頂級男演員。
尷尬的是,《外太空的莫扎特》似乎也驗證了那句「相見不如懷念」。

這部電影,本是備受觀眾期待的「外太空三部曲」之一,上映後卻口碑崩塌,票房也不理想,21天只有2.2億。
本以為它會坐穩暑期檔的第一把交椅,結果才上映半個多月,就已經看不到多少排片了。
陳思誠血厚,栽了這麼個跟頭沒啥。
可對於黃渤來說,這個打擊就有點大了。

這幾年黃渤真的不走運。
皮哥已經記不清上一次他主演的電影票房大賣,是什麼時候了。
在「百億影人俱樂部」裡,他的票房含金量,也被很多人看不上。
從9年前算起——
《西遊降魔篇》大賣,被認為是沾了周星馳的光;

《心花路放》大賣,被認為是和徐崢、寧浩捆綁;
《尋龍訣》大賣,被認為是蹭了IP的熱度;
《瘋狂的外星人》大賣,被認為是和沈騰組成雙核,外加寧浩自帶的「瘋狂」buff;
對了,還有《穿過寒冬擁抱你》這樣的拼盤電影……

最能打的,反而是他的導演首秀《一齣好戲》,票房13.55億。
不過放在當年上映那一年,也排在了十名開外,主演裡還有王寶強、舒淇、張藝興這樣的大咖。

說完票房,黃渤在演技上的困境更讓人唏噓。
過去黃渤的表演,給人的感覺是充滿靈氣的。

無論是《瘋狂》系列裡的黑皮、黃毛,還是《鬥牛》裡的牛二,或者《殺生》裡的牛結實,都讓人感覺到撲面而來的生命力。

那種不加修飾的野性是黃渤過去的金字招牌。
可是這些年,黃渤的名氣越來越大,那股角色裡的靈氣,卻仿佛消失了一般。
問題出在哪裡?
1、
陳思誠的預言
我們大可不必苛責黃渤。
發生在他身上的「不幸」,其實反映的是整個中國電影市場的悲劇。
從某個角度來說,過去這幾年,中國電影崛起的同時,也在走一條下坡路。

90年代,《霸王別姬》《活著》這樣的作品被刻上了豐碑;
00年代,《鬼子來了》《可可西裡》這樣的作品被載入了影史;
10年代,《讓子彈飛》《我不是藥神》這樣的作品一直餘音繞梁。

到了這幾年,再看大銀幕。
已經是喜劇、科幻和主旋律電影滿天飛了。
國產電影的今天,也讓皮哥想到了陳思誠在2年前的一番預言。
2020年的北影節論壇上,陳思誠描繪過院線電影的未來方向。

他說一部電影要想在院線取得成功,應具備以下兩個特點之一:
其一是能反映強大的電影工業實力,那種沉浸式的視聽體驗是在家看流媒體無法取代的;
其二是電影故事能反映當下的現實,能引發觀眾廣泛共鳴。
陳思誠這話確實沒說錯。
第一類重工業的視覺大片,諸如《長津湖》《流浪地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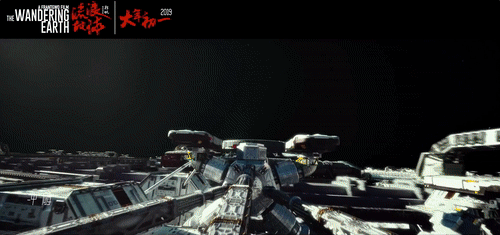
雖然分屬不同賽道,但票房都取得了成功。
第二類電影,說的就是「現實主義題材」。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不是藥神》。

這兩類電影方向,都有難度。
前者是製作層面的技術原因,後者則需要面對審查層面的「技術原因」。

只是第一種難度可以解決,無非花錢、花時間,搞技術升級。
第二種難度,很容易讓人望而卻步。

所以當下越來越多的導演,都會選擇第一條賽道,用「大片路線」來博取票房。
但這種追逐,不可避免地讓中國電影走入了一條窄胡同。
這幾年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
大熒幕的色彩越來越華麗,特效越來越逼真,堆積的明星越來越多。

但那些動人的好故事、好劇本,卻越來越少。
沒有好故事、好劇本,再頂級的演員也只能在商業片的俗套裡打轉。
商業片裡,他們的表演依舊合格,會讓你哭,讓你笑。
但很難再「封神」。
原因就在於他們的表演少了那股力量,這股力量恰恰需要以現實的厚重,為支撐。

在2019年之前,國產電影的票房節節攀升,漂亮的數字可以掩蓋國產電影內容的匱乏,整個影視行業也歡欣鼓舞。
但是疫情之後,電影市場萎靡了,中國電影的弊病就暴露無遺了。
所以,我們說黃渤的困境,本質上也是中國電影的困境。
2、
沉默的大多數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靠誰?
當然不能靠資本,資本也沒義務幹這事。
還是需要靠導演。
在皮哥印象裡,中國有才華的導演並不少。
可慢慢地,他們就成為了「沉默的大多數」。
比如郝傑。

他一出道就拍出了《光棍兒》《美姐》這樣農村題材的影片,尺度之大膽,想像力之生猛,讓陳凱歌都感到震撼。
他拿到了FIRST青年電影展的最佳導演獎,頒獎時當著徐崢的面擰脖子歪頭,說著一些「狂妄」的話,一副睥睨天下的樣子。


可隨後迫於壓力,他轉型拍了商業片《我的青春期》,結果口碑票房都很一般。
郝傑直接抑鬱了,在影壇消失了6年。
再出現時,當年那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已經不見了。
他頭上添了幾縷白髮,整個人畏畏縮縮,和演員說話都很驚恐,拍的東西大家也看不懂了。

還有張猛。
出道就拍攝了《耳朵大有福》《鋼的琴》這樣的現實題材影片。

他的作品沒有那麼強的批判性,關注的都是小人物身上的小事兒,充滿了生活情趣,範偉、王千源也通過出演他的電影,成為了公認的演技派。

可隨後張猛也轉型了。
他做了製片人,拍了《不期而遇》這樣的爛俗商業片。
2019年他又回歸本色拍攝了《陽臺上》,卻沒有當年的味道了。

還有管虎,黃渤真正意義上的貴人。
《鬥牛》《殺生》兩部充滿野性張力的影片,展現出了黃渤的最強演技,也讓他順利成為了金馬影帝。

後來管虎又拍了《廚子戲子痞子》《老炮兒》等電影,野性越來越少,商業味兒越來越濃。
《八佰》《金剛川》之後,他一躍躋身至主旋律商業片導演陣營。

所以中國不缺有才華的導演。
只是這些導演的結局無非有二。
一是像賈樟柯一樣,堅持走「曲線救國」之路,牆裡開花牆外香,靠國外拿獎在國內求得立錐之地,但這條羊腸小道太過曲折不好走。

二是迫於壓力,或者主觀意願,轉型成商業片導演。
大部分藝術片導演,都會走上第二條路,只是堅持的時間長短不同。
為什麼他們拍商業片,就會有局限?
比如管虎拍《八佰》,影片裡設置的幾種士兵角色,從性格到表現,其實都是可以想像的。

即使來的是王千源、姜武,表演也很難逃脫模式化。
商業片就是這樣,從劇本到角色,那層殼是去不掉的。
3、
被動的演員們
當導演都開始投靠「主流」時,越來越多有特色的演技派,也只能隨波逐流。
黃渤不是個例。
典型的還有秦昊。

曾幾何時,對藝術「清高」的他堅持只演文藝片:「每年只拍一部電影,第二年肯定會入圍國際電影節。」
面對上門邀請的電視劇、綜藝,他悉數拒絕。
「我是按照一個藝術片導演的要求,來要求自己的。」
可秦昊接下來說的這句話,令人心酸:
「直到我看到我尊重的大導演們,都開始擁抱流量了。在那一刻我覺得,我被他們騙了。」

他還在死等電影好角色,留給他的路,自然也就越來越窄。
後來在周迅的勸說下,他也「想通了」:
「連周迅這個級別的演員都碰不到好的劇本,我也就別擰巴了。」
於是他接了網劇。
秦昊算是運氣比較好,遇到了「張東升」這樣一個角色。

相比之下,餘男就有些落寞。
當年和某導演談戀愛的時候,她接連出演了《驚蟄》《月蝕》《圖雅的婚事》,全都是現實主義力作,餘男的特點被完美呈現。

之後她又出演了《無人區》《全民目擊》這樣的好電影。
那厚嘴唇和銷魂的眼神,充滿了野性的美。

到了這幾年,她拍的作品都是什麼?
豆瓣評分3.8的《上海王2》,不到6分的犯罪劇《謊言真探》,和保劍鋒主演的《人質列車》。

這些作品中,她的靈氣也消失了,只能常規地把劇本演給觀眾看。
還有周迅和章子怡,咖位都大,獎項夠多,演技被多次肯定過了。
因為沒有電影好劇本、好角色,轉頭去演電視劇。
一部《如懿傳》,一部《上陽賦》,兩人毫無靈氣,呈現出的效果也是老氣橫秋。


看吧,當好演員遇不到好劇本,縱使你是影帝、影后也白搭。
秦昊面對鏡頭笑著總結:走出舒適圈,打開自己,我看見了更大的世界。
但「張東升」這樣的「天作之合」不會是常態。
秦昊還能「挺」多久,沒有人知道。
4、
一些「糟糕的事」正在發生,不過,「改變」也正在發生
過去的每一代導演都帶著強烈的特質。
張藝謀和陳凱歌為代表的第五代導演,他們的特點就是注重人文情懷,拍的影片大都講的是家國天下;

賈樟柯和王小帥為代表的第六代導演,他們的特點就是更強調個體意識,所以他們的影片都充滿了批判和反思。

而新時代導演很難被定義。
非要定義就是他們都很自由。

自由的代價,就是這批導演不約而同奔向了商業片的陣營,在這個速食年代,很少有人堅守在藝術片的陣營裡。
但中國電影的進步,不能只靠商業片的成敗來定義,其他藝術電影同樣重要。
還是拿賈樟柯來說。
2006年,他的《三峽好人》遭遇張藝謀的《滿城盡帶黃金甲》,他大聲疾呼:「崇拜黃金的年代,誰還關心好人?」

今年主旋律影片票房大賣,又是賈樟柯站出來說:「不能把中國電影只做成主旋律影片的專賣場。」
在皮哥看來,這樣振聾發聵的發言還是太少,導演裡「沉默的大多數」應該有所表達。
尤其是新生代的導演,他們夠生猛,他們敢想,他們能闖。

不過我們不必過於悲觀,很多電影人已經意識到了這些困境,我們能看到很多改變。
第一大改變,就是「老帶新」,全面鋪開。
比如我們看到這兩年多了《開拍吧》《導演請指教》這樣的挖掘新人導演的綜藝,儘管褒貶不一,但像郝傑這樣曾被打擊到抑鬱的導演有了重新出頭的機會。
比如我們看到劉德華用「亞洲新星導計劃」挖掘了寧浩,寧浩成名後又用「壞猴子72變電影計劃」挖掘出了文牧野,他還幫助了郭帆,郭帆又在自己的《流浪地球》片尾致敬了劉德華。

徐崢那邊也不閒著。
去年他聯合吳京、郭帆開啟了「金鑰匙創投計劃」挖掘華語影壇創作新人,而他扶持的90後女導演邵藝輝,在去年自編自導了《愛情神話》,也收穫了極佳的口碑。

即使票房一般,但這部作品帶有的藝術探索,是當下中國影壇急需的。

第二大改變,就是「終端載體」變得更多了。
2016年,中國藝術電影放映聯盟正式啟動,目的就是給藝術電影更多機會。
最初影廳只有100個,現在規模已經越來越大,遍及各大城市。

當下觀眾對藝術電影,是有一定需求的。
比如《掬水月在手》這樣的藝術電影,通過藝術院線放映後,也取得了近1000萬的票房。
去年的《東北虎》,最近上映的《隱入塵煙》都是現實主義題材的佳作,演員演技驚豔,也都取得了近2000萬的票房。

製片人不需要再用下跪的方式,來爭取排片。
編劇願意沉下心寫,導演也敢放心地拍,演員也有表達演技的窗口。

只有這樣,未來我們再回憶起現在的年代,回想起的,才不會只是那些視覺大片。
最後回到黃渤。
他就是中國電影具象化的體現,有過巔峰,有過輝煌,如今的困局,我們為他感到唏噓。

但又不必過於悲觀。
很顯然,黃渤已經意識到了問題。
他和曹保平、周迅合作的《涉過憤怒的海》,和管虎合作的《狗鎮》已經蓄勢待發。


這些影片或許能幫他找回丟失已久的野性。
他不是獨行,他的身後是跌倒後剛剛爬起來的中國電影,一些糟糕的事在發生,但一些改變也在發生,而這些改變,正是中國電影真正崛起的希望。
文/皮皮電影編輯部:一粒雞
©原創丨文章著作權:皮皮電影(ppdianying)
未經授權請勿進行任何形式的轉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