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吳京和章子怡的感情戲(吳京演出了滄桑英雄)
2023-08-05 13:06:49 4
我敢打賭,這大場面你肯定是第一次見。
什麼大場面?

災難片冒險片你看得多了,但《攀登者》一開場這20分鐘,一場戲就拍出1960年中國攀登者首次攀登珠峰的時代背景、細節、人們的心理狀態,甚至包括這場攀登中的遺憾。我敢說,你沒見過。
說實話,看之前,我心裡是忐忑的。這個故事,太珍貴,太動人,太值得拍,所以也太怕拍砸。

1960年5月25日,中國登山隊以搭人梯的方式越過了珠穆朗瑪峰的「第二臺階」,首次實現了人類從北坡登頂珠峰。但是,這次攀登卻因為沒有留下在峰頂拍攝的360度影像,而不被西方登山界承認。1975年5月27日,中國登山隊再次成功登頂,並測量出珠峰的精確高度為8848.13米。
這就是電影《攀登者》故事的開始:1960年,一次偉大而令英雄們有些憋屈的登頂。

而影片的主線,說的是第二次登頂。
我知道你們都聽說過這部電影,也知道它預售已經破億的事兒,還知道你們擔心的什麼,都別藏著掖著,說出來——對,李仁港。這位一出道就拍過《黑俠》的導演,上部大片,是《盜墓筆記》。
三年之後,徐克 李仁港,能把這個中國好故事拍出來嗎?
我就一句話: 李仁港這次沒用錯吳京章子怡,更沒浪費中國好故事。
徐克 李仁港,沒砸!先說一句,以歷史為底座,有阿來的劇本打底,《攀登者》絕不是一部好萊塢式超級英雄大片,也沒有一個光環附體、無往不利的英雄角色。

電影裡,只有純藍蒼穹下,皚皚白雪上,一群大寫的,有血有肉的,隨時可能遇險犧牲的人。
這是李仁港這次最令我驚訝的地方:這麼熱血的故事,李仁港卻是收著拍的。鋒芒不張於外,卻自有內力澎湃。

這股電影的內力,源自於足夠精彩的故事。
但別忘了,還有徐克。
徐克者,武俠也。
哪個少年沒看過徐克的武俠片呢?如果說《智取威虎山》是一次經典題材的武俠式變形,那麼《攀登者》其實也埋藏著徐克放不下的俠骨柔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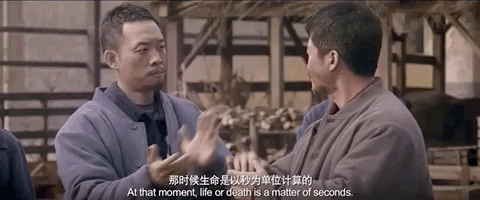
可能有人說我扯,登山大片,顯示題材,俠什麼俠,懂不懂?但中國人的俠義情懷,難道只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隱忍十五年,眺望同一座雪山,只等15年後,為當年的攀登者們正名,這不是俠?
是兄弟,也有恩仇,但在大義面前,放下往事昂然向上,不以禍福趨避之,這不是俠?
對,我說的就是本片兩位主角的故事——吳京和張譯。
他們都是登山隊的「兩朝元老」。
電影在這兩個角色身上,不僅埋下了行動上的艱難、視覺上的驚險,也就更放進了時代和歷史的厚重感。

這是影片在第一層行動的攀登之外,設置的關於攀登的第二層含義——攀登者心靈的攀登。
從第一次攀登到第二次攀登,15年,一個問題至關重要:信不信?
第一次,他們明明完成了世界級的壯舉,有人卻不信。
在蟄伏了十五年之後再次挑戰極限,是攀登那座高峰,也是要攀登自己留下了15年的心理障礙的高峰。
對於吳京的角色來說,是從1960年開始15年的等待,在憋屈、寂寞中等待機會。他總算等到了。
對於張譯的角色曲松林來說,由於瘸腿,第二次攀登無法再朝著珠峰邁步,只能擔任登山隊教練,負責第二次登頂珠峰的訓練工作。他只能藉助別人的腳,完成登頂的夙願。

電影的動人之處在於:它糙中有力、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將視角放置於一群普通的人,帶著煙火氣的、土裡土氣的,卻非常親切和真實。
誰能證明中國隊員登頂成功了呢?
只有珠峰。
登上去,才有資格讓質疑者從此閉嘴。

故事的張力就在於,讓影片擁有了兩個不同年代攀登之間的對照,甚至於可以說,是憋著一股勁兒:上一次,200人用血肉之軀託舉起的高度,有人拒絕承認。
那好!
1975年,中國登山隊再次登頂,並且測量出珠峰的高度。
在「第二臺階」留下一把金屬梯,被後來許多國家的登山家蹬著攀上珠峰,它被稱為「中國梯」。
這麼個盪氣迴腸的故事,極其容易犯下的錯誤,就是過火,因為這個故事本身太燃,太動人,只要稍不克制,就會帶出不真實感。
而李仁港這次交出答卷不僅是及格的,甚至可以說是優秀的,在多數時間裡,他的敘事都把最煽情的故事用克制的方式表達出來。

不動聲色間,打動人心。
但,影片又保持了敘事的流暢度,該有的衝突、浪漫、緊張、一波三折、反轉,甚至是討巧的小細節,都不缺。
故事講好了,電影就穩了。但要讓電影燃起來,還得看電影的視覺場面,行不行。
《攀登者》,燃!別忘了還有徐克。
徐克有個習慣,做監製從不摸魚,他會向電影裡注入自己的風格,因此《攀登者》的動作場景,很自然地帶入了徐克式的俠風。
而《攀登者》的出現,不僅很好地填補了華語片這類極限冒險大片的類型空白,還非常好地向這種類型注入了中國電影的風格,而不是對好萊塢式同類作品視覺風格的套用。
這一點,就厲害了。
攀登類大片有什麼?
高度。撲面而來的極限高空危機。

速度。須臾之間,山崩形成。
當然,還有極限環境最恐怖的破壞力。
白雪茫茫,人與環境,殊死一戰,怎麼拍才好看?
看《攀登者》充滿俠氣的場景。
眾人之力,飛躍懸崖。

雪坡之上,騰挪翻滾。
這是一場俠客對決,而最大的對手,就是自然。
比起明刀明槍,自然永遠是一位暗器高手,低溫、風雪、懸崖、峭壁,全都可以是殺人於無形的武暗器。

徐克和李仁港的鏡頭下,我們的登山隊員們,則成為笑傲風雪的群俠。
隨時隨地都會發生的雪崩到來?迎風不懼。
冰裂縫出現?飛架天梯。
傾斜度極高的雪坡?決不腿軟。
俠客聯手,總有犧牲。
張譯飾演的曲松林,為了搭人梯為隊友減重,脫下自己的高山靴再攀上巖壁,之後,他不得不切掉了十根腳趾。
在片中,我們就能看到他赤腳攀巖的場景,熱血到觀眾流淚。
曾被視作最後的武俠大師希望的李仁港,一直是港片中的視覺高手。
這一次,他真的充分利用了登山時的縱向環境,尤其是那些甚至會大於六十度的坡度,去營造視覺構圖,製造畫面張力、渲染緊張感。

而有些場景,有能讓人分明感受到徐克的存在。
片中有一幕讓人印象深刻,方五洲帶領年輕一代攀登者首次向珠峰發起挑戰過程中遭遇風暴,十幾位隊員將自己和梯子捆綁在一起,掛在一塊山石上,狂風暴雪肆虐整整一夜,大家就這樣在冰天雪地中艱難度險飄搖了一夜。

這一幕可以稱得上《攀登者》最為精彩的動作戲之一,人如衰草,命若遊絲。動作、冒險及現實故事完美結合,這不是好萊塢式同類大片能拍出的視覺想像力,而是標準的徐克式的武俠風格,只有我們華語大片,才能拍出這麼盪氣迴腸的精彩場面。
雙劍合璧,演員用命,動作戲穩了,電影的視覺場景,成了。
吳京表演太令人意外、章子怡角色命運唏噓,而胡歌井柏然的結局戳爆我淚點《攀登者》第三件做對的事,就是讓人物立住。
人立住了,細節才耐得住咀嚼。
男一號吳京,飾演方五洲。
「戰狼」?很容易注意這一次他表演的變化。
依然是演英雄,卻多了一種巨大的滄桑感。

臉是糙的,眼神剛開場是疲憊的,但又藏著堅定。
方五洲這個角色,算是登山隊某種意義上的精神領袖,但《攀登者》絕不是一部個人英雄化的作品, 這個角色,其實和張譯的曲松林構成了某種呼應。
相知相惜、又相愛相殺。
當年完成了又不算徹底完成的登頂,成為兩個人一輩子的心結,有一場戲是曲松林質問方五洲攝影機的事兒,他就站在那兒,沒有反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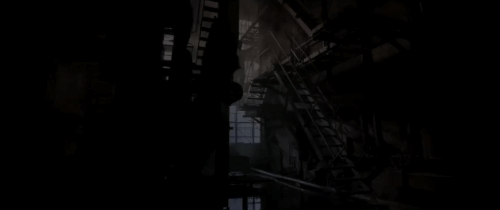
兩個大男人的性格差異,通過這場戲展露無遺。
一個隱忍,一個堅韌。這種英雄惜英雄背後,都是戲。提醒你重點觀賞一場喝酒戲,有多燃,自己看。張譯這壺酒,是陳釀。

吳京這次表演最打動我的,還是那種有別於過往全程高燃的舉重若輕,有一場戲,是方五洲在劇中為了挽救攝影機而被雪崩壓在下面,被刨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為他死了,急救後他一下子突然甦醒,說了一句「我剛才……歇了一下」。
除了表演變化,這一次,吳京還要在電影裡談一場重量級戀愛。

當時那個時代,表達愛意並不像現在這樣便捷直白,吳京也成功把方五洲的那種內斂、寡言下的愛意表現得很妥帖,而與他演出這種帶有生活氣愛情戲的,正是章子怡。
女一號章子怡,角色名徐纓。
登山隊氣象專家,任務是觀測珠峰天氣,幫助登山隊找到適合的登山機會。

導演李仁港說,吳京與章子怡的搭配,是「喝紅酒吃鹹肉」。
鹹肉,糙、硬、有力道。
兩人上次合作還是徐克2001年的《蜀山傳》,沒有太多對手戲。
而這一次的章子怡,也是在有限的時間內很好地演出了一個雪山女神的角色成長和命運轉折。
尤其是人物的結局,應該會讓許多人心裡咯噔一下為之動容。

同樣驚豔的,還有井柏然和胡歌這些相對新一代的演員。
而兩人悲劇性的結局也相當令人動容,我相信都會引發許多人落淚。

也真是通過這幾個命運充滿遺憾的角色,讓我們看到本片的人物,不是宣洩情緒、強推主題的工具。
因為人和自己內心的角力,人攀登內心高手的過程,才是類型片真正永恆的法則。
看到最後,人們愛的不僅僅是飽滿的人物與精彩的設定。
更在於,那人物身上汩汩流淌的,強大的精神力量。

由於徐克李仁港的存在,影片人物又如很多群俠片處理的群俠一樣,幾個角色有故事,有過往、相遇、各司其職並完成任務,也走向不同命運的結局。有些是苦盡甘來,有些無比唏噓,我一個中年大叔,都哭暈了好幾次。
也因為這些人物塑造充滿回甘,更讓整個故事具有了某種回味,我想,這就是人物的力量,也是源自人物原型的了不起。
這部電影,配得上我們的珠峰英雄,這比多高票房都重要英雄無需仰望,英雄要的是尊重。
珠峰英雄的那份豪情與尊嚴,遠超戲劇。

這也是我認為電影最核心的考問,也是最關鍵的一份答卷——這部電影,配不配得上珠峰英雄們?
1960年,國內的登山隊還缺乏訓練,缺乏裝備。登頂,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登頂珠峰的道路,最大風力可達每小時189千米,相當於在颶風中行走。
氣溫可達零下73攝氏度,氧氣含量也僅有海平面的三分之二。更不用說在過去的十幾年裡,有280多人因為挑戰珠峰失敗而把自己的生命永遠留在了這裡。
1960年,浩浩蕩蕩200人,走到最後,只剩下19人。
到達了北坡海拔8680米處的「第二臺階」的時候,僅僅只剩下4個人——王富洲、屈銀華、劉連滿和貢布,英國人說「這是任憑是飛鳥也絕對逾越不了的地方」。
可他們一路繼續往上攀登,僅僅只剩下4個人,英國人說「這是任憑是飛鳥也絕對逾越不了的地方」。
到達海拔8680米處的「第二臺階」時,他們發現橫亙在眼前的,是高達4米的巖石峭壁,沒有攀緣支點,鋼錐也無法打進去,看不到登上去的可能。

沒有支點,那就人肉作支點。
可就是這飛鳥都無法逾越的珠峰北坡,被隊員貢布、王富洲、屈銀華三人,在隊友劉連滿「搭人梯」的幫助下,成功逾越了。
他們將五星紅旗插上世界之巔,也是第一次夜間無氧登頂珠峰。
當年的珠峰英雄,不是所有人都能回來。回來的,也不一定全身而退。
而如今,英雄們多數已經凋零。

突擊隊長王富洲上山時體重是160斤,下山後只有101斤。
2015年7月18日,王富洲,北京逝世,享年80歲。
屈銀華在爬人梯的時候,為了給劉連滿減輕負擔,主動脫下了4公斤重的長靴,最後在寒風中凍壞了雙腳,下山之後便接受了截肢。
在《攀登者》首映時,女兒屈虹回憶往事:覺得父親很窩囊,走路得時候像一隻鴨子,缺乏男子漢氣概,我都覺得有些難為情。
2015年9月19日,屈銀華在北京去世,享年82歲。
當年為隊友搭人梯的劉連滿在遺書中寫道——「王富洲同志:我怕沒有完成任務,對不起人民。這裡你們留給我的氧氣和糖,你們用吧!或許它能幫你們快些下山,把勝利的消息報告給祖國人民,永別了!」

2016年4月27日,劉連滿因雙下肢股動脈血栓引發併發症,在哈爾濱去世,享年83歲。
1960年的四位珠峰英雄,迄今為止僅剩下貢布尚在人間,家人瞞著他,不給他知道其他戰友的消息。
即使是英雄們的親人,也是直到長大,才知道他們所經歷的一切。
英雄,並不總是和光環相伴。登頂結束後,一切歸於平靜。但英雄們創造的史詩就在那裡,等著有人去呈現。
在《攀登者》之前,中國並沒有同類題材的電影出現,無論是在製作規格上還是在拍攝難度上,都稱得上是國產類型片的一次極大挑戰。結果是電影人們接到拍攝任務到最終完成影片製作只用了十五個月,在幾乎不可能完成的條件下創造了紀錄。

為了完成這部電影,吳京遠赴崗什卡雪峰進行登山學習及訓練,並請了職業登山家做指導,進行了半個月的極寒訓練。
由於常年拍戲他腿上的舊疾復發,連長時間地站立都變得困難,他戴上夾板,拄著拐杖接著拍。
張譯為了讓外形更符合片中的角色形象而「自虐」式減肥,曾經一天只吃兩根黃瓜,並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堅持「瘸著腿」走路。
曾經去到拍攝現場進行探班的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陳道明曾說:「這是真誠的表演,處處都有充滿力量的細節!」
從影片呈現的效果來看,雪山的特效、質感,給人身臨其境的臨場感和壓迫感,仿佛將觀眾代入到極端環境中去。但更重要的,還是影片塑造了一群錚錚鐵骨的珠峰英雄。

在那個溫飽都成問題的年代,登山究竟是為了什麼?影片中吳京飾演的方五洲的回答是:「幾億人如果只想著吃飯問題,那我們的民族又能有什麼出息?」
為珠峰的懸崖之上,沒有神話,但有一群熱血兒女為國登頂。
監製徐克,在海拔5200米的高度說:「1960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從(珠峰)北坡登頂的壯舉正是由中國攀登者完成。既然是我們的高山,我們的腳就要親自踏上去。」
影片中有一幕讓我印象深刻,天寒地凍,漫天風雪中,精疲力盡的登山隊員們緩慢地舉起我們的國旗。天地之間,大寫的中國。
沒錯,包括配音、剪輯、過度飽和的配樂,影片尚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不過,這些都並不重要。
有沒有發現,這些國慶檔電影爆款的演變,背後是中國人的關注點在不斷向遠處延伸——
從身邊開心麻花喜劇式的家長裡短;到這個國家了不起的史詩,《攀登者》是一次更高的眺望。

作為影迷和觀眾,能在大銀幕上看到這樣一部兼具誠意和水準的電影,也是我們最大的幸福了吧。也期待有了《攀登者》完成這次攀登後,未來會有更多同類型的國產主旋律大片出現在我們的視野中。
主旋律大片不僅需要昂揚主題,同樣需要精彩的表達方式與緊張又充滿吸引力的敘事方法,這才是一部成熟的主旋律大片該有的。
這也是我力挺《攀登者》的原因,精彩的故事,方法是很商業的、很類型片的、是可看度非常高的,一群出色的演員,再輔以適當的煽情與動作元素,到最後,又讓人們感受到打通內心的熟悉的情感呼應和共鳴。

英雄們需要的不是仰望。而是理解和尊重,以及,不被遺忘。
沒有人想走下坡路,人人都想走上坡路。之所以要登山,因為山就在那裡。
對於當年的珠峰英雄如此,對於今天的中國電影人也是如此。
這部電影,真配得上我們的珠峰英雄,這比再高的票房都重要。
向每一位「攀登者」致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