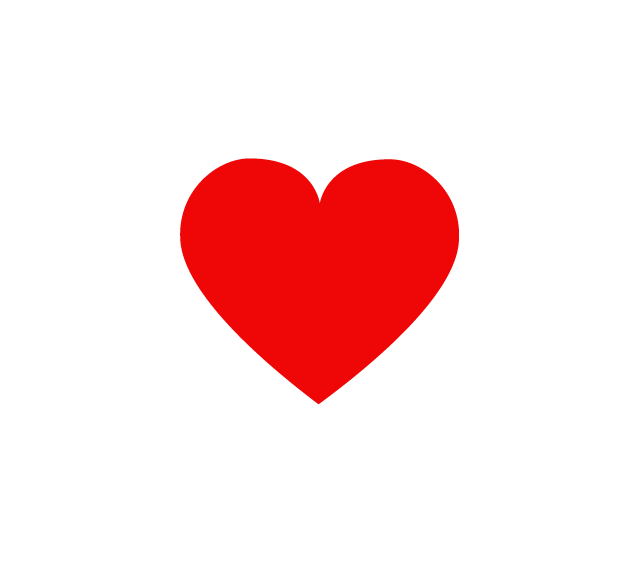驚蟄之諜海深圳的結局(科幻的深圳吳巖的結局)
2023-06-17 14:53:26 2


一北一南,一人一城,本無交集。
如果給18歲的吳巖一臺時光穿梭機,他會很高興遇到2022年仍堅守科幻陣地的自己,但他也許猜不到,抵達的目的地叫深圳。▃
世界讀書日到來的前一天,晚8點,中心書城的多功能廳裡開啟了一場周五書友會的線上直播。對著鏡頭,主持人介紹今天的嘉賓——「當代中國科幻文學的大家之一,吳巖老師」。
頭髮有些灰白,身穿棗紅色POLO衫的吳巖笑容可掬,點頭致意,雙手握著話筒舉至額前,比了一個類似的抱拳禮,一張口標準的京片子,語調輕快,儒雅中透著可親。
主持人說,當活動計劃邀請科幻作家時,首選就是吳巖。而這句話放在深圳大部分以科幻為主題的活動中皆可。無論是平常大大小小的文化沙龍、講座,還是像首屆鯤鵬全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獎這樣新興的賽事,甚至是深圳建築界的重要盛事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都能看到吳巖的身影。
1979年,17歲的北京少年吳巖人生第一篇科幻小說發表時,「深圳市」這個行政建制才剛誕生。
1980年,18歲的吳巖立志從事科普和科幻創作,深圳也在建設經濟特區的賽道上開始了奔跑。
一北一南,一人一城,本無交集。如果給18歲的吳巖一臺時光穿梭機,他會很高興遇到2022年仍堅守科幻陣地的自己,但他也許猜不到,抵達的目的地叫深圳。
成為深圳人
因為疫情關係,吳巖工作和居住的南方科技大學從今年春節起就實行了封閉式管理。這場直播,是他幾個月來首次重返現場,可惜他的觀眾們仍然在線上。
雖然長時間宅在學校裡,但吳巖並不是很在意。南科大校園中有九山一水,大沙河從園中緩緩流過,山上到處是鬱鬱蔥蔥的樹木,美得像個大公園。吳巖白天忙於工作,晚上時不時就去山上散步,悠然自得。
其實,到深圳生活,吳巖自己也沒料到。他當初覺得北京霧霾有點重、人有點多,想尋個南方的城市做兼職,先想到的是海口。2017年,南科大人文科學中心主任陳躍紅(現任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邀請吳巖來講課,「我覺得深圳也是個熱鬧的地方,我其實並不想來。」吳巖說,來了後卻發現深圳空氣挺好的,校園大、漂亮且安靜。所以半年後,陳躍紅問他願不願意正式加盟時,他被能住在校園中這個條件誘惑就欣然答應了,辭去了當時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公職。
除了生活環境符合自己的預想,更重要的是吳巖想做的事在深圳得到了大力支持。
1991年,吳巖在北師大首創科幻文學課程,2003年,他開闢國內第一個碩士研究生科幻專業方向,又於2015年將該方向提升為博士生研究方向。2017年底,他在南科大主持成立了國內首家研究想像力本質、開發、未來預測,以及科普和科幻創作發展的跨學科研究機構——科學與人類想像力研究中心。
通過科學與人類想像力研究中心,吳巖想完成三個目標:一是進行想像力的基礎研究;二是開展對未來的探索;三是研發新的科幻作品,培養新的科幻作家。
四年多的努力,讓研究中心收穫了喜人的成果。研究中心創立以來已出版《科學幻想:青少年想像力與科學創新培養教程》《中國科幻文學沉思錄》《20世紀中國科幻小說史》等書籍。由吳巖引薦來南科大的青年教師、科幻作家劉洋,創作的《火星孤兒》正在進行電影、電視劇的改編拍攝。而吳巖自己也交出了一本《中國軌道號》,去年斬獲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
這部作品吳巖醞釀了20年。上世紀末,國內剛剛繁榮的科幻文學遭到質疑,當時吳巖就在想,能否寫一篇看起來非常真實,但卻根本沒有發生過的故事,令各種質疑都在作品面前失去意義呢?
吳巖想到了中國的載人航天事業。那個年代有關中國的航天秘密,他只能從偶爾出現的報導、回憶錄、報告文學作品中找到,於是他購買了大量航天相關的雜誌、科技創新著作,甚至成功進入一家航天科研所裡買到了一些內部資料。但是吳巖前後寫了幾稿都不夠滿意,他陷入了苦惱,幾乎停止了創作。
來到南科大後,一次偶然機會吳巖又想起了多年前被擱置的題材。從風雲、北鬥到嫦娥探月,從神舟、天舟再到天宮空間站,在這20年裡,中國的航天事業已經有了飛速的發展。身處一所科技大學中,吳巖不僅隨時可以在校園裡聽關於科技的講座,平時也常與科學家們交流。「回歸」創作,水到渠成。
從無變有
吳巖移居深圳的消息在當時的深圳科幻圈裡引起了一陣騷動。科學與幻想成長基金髮起人馬國賓就特意組了個飯局,想邀請吳巖與大家認識一下。可惜,那天吳巖有事沒能前往,讓他現在想起都頗感抱歉。不過兩人還是加上了微信,並在不久後從網友走到了線下見面。
2018年,吳巖邀請了一位義大利科幻作家來訪,但他自己不熟悉深圳,校園轉完了也不知道去哪,就拜託了馬國賓,問他能不能當嚮導,帶他們轉轉深圳。馬國賓一口就應下,領著他們去了東部華僑城的大華興寺,吃了齋飯,下山又去了出名的華強北,外國作家玩得很高興。
此後,吳巖和馬國賓慢慢熟悉起來,吳巖親切地叫他「小馬哥」, 給他介紹了不少國外的科幻資源,而馬國賓也常常邀請吳巖參加科幻主題活動,兩人的團隊合作了至今一年一度發布的《中國科幻產業報告》。
「小馬哥這些人其實是深圳的特色,他們一定要把(科幻)這件事做起來,我覺得這些人代表了深圳。」吳巖說,正是有了馬國賓等一批科幻迷的推動,才讓深圳的科幻從無變有。
馬國賓的本職工作是朗科科技執行董事,這個在深圳長大的80後從小就是科幻迷。2014年,他去參加上海的一個科幻頒獎活動,一方面是為了認識科幻作家劉慈欣,另一方面是出於工作的需求,「我需要像科幻作家那樣去思考未來,廣泛的興趣愛好跟學科知識可以支撐我對項目的判斷。」他說道。
馬國賓得償所願,他還清楚記得當時的場景,他和劉慈欣一起抽菸、吃泡麵,交流的過程中,時不時有人找劉慈欣籤名。馬國賓送了他一套公司的產品,劉慈欣說自己對科技公司也感興趣,是他創作的源泉。
之後,馬國賓又趕赴另一個在北京的科幻頒獎活動,但他沒想到去的差不多是同一批人,「從我做投資的直覺,中國的科幻可能出現問題了。」他說,相比美國2億多人中有2000多位還在寫作的科幻作家,中國14億人中,在當時活躍的且有出版社願意出書的作者不足10人,而且多數是兼職寫作。「聽一些作家介紹說寫言情穿越的小說每一千字給800元,科幻小說每一千字給80元(當時的行情)。」
回到深圳後,馬國賓找到一群同為科幻迷的科學家、投資人、科幻作家、工程師、媒體人及公益人士,在深圳市社會公益基金會的幫助下,於2015年成立了中國首支致力於推動科幻產業發展的公益基金——科學與幻想成長基金,這也是至今國內唯一一支。
近幾年,隨著政府和企業對科幻產業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科幻迷的群體也在壯大。馬國賓說,一開始組織科幻主題活動,線下只有二三十人參加,現在能有幾百人,尤其很大比例是科技公司的理工男。「可以說科技園是科幻迷大本營,提起《三體》大家都很熟悉。」
「你到任何城市,都會發現科幻迷中很多來自科技企業,但是深圳的比例會更大。」吳巖說,這也跟深圳的科技企業數量多有直接關係。
深圳被稱為「中國矽谷」,華為、中興、騰訊、大疆等企業匯聚於此。據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發布的《2021年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深圳—香港—廣州城市創新集群位列全球第二。分析認為,深圳不僅通過體制創新推動科技創新,還將香港的金融創新資源、廣州的基本服務資源,以及整個珠三角地區的發達製造業和先進位造業方面形成的資源整合到一起,使得這一區域成為全球科技創新資源比較密集的地區。
如果將深圳的科幻文化比作一棵樹苗,無疑是載種在了最肥沃的土壤之中。
下一個劉慈欣
3月9日晚上,吳巖發了一個朋友圈:「記住今天的日期。科幻界盼望那麼多年的科幻委員會成立了。中國科幻作家有了自己獨立的委員會,走向新時代了。」
在這一天公布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十屆專門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中,第一次出現了科幻文學委員會,主任為劉慈欣,吳巖的名字在副主任一職中。
從被批判到被肯定,中國科幻走過大起大落。隨著《三體》《北京摺疊》在國際上獲獎、《流浪地球》電影熱映,中國科幻迎來了發展的黃金時期。從2018年至2021年發布的《中國科幻產業報告》對比顯示:2017年中國科幻產業產值超過140億元人民幣,2018年是456.35億元,2019年是658.71億元、2020年是551.09億。雖然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稍有回落,但四年總體趨勢向上。其中科幻閱讀市場2017年產值總和9.7億元、2018年產值總和17.8億元、2019年產值約為20.1億元、2020年產值為23.4億元。
而在深圳,從一個小小的微信群就能折射出這個時代的變化。2018年左右,在吳巖的建議下,馬國賓建了一個「深圳科幻作家群」,當時只有10多人,後來有旅居深圳的科幻作家、本土正在成長中或者已經嶄露頭角的科幻新秀,甚至還有省內其他兄弟城市或港澳的作家、研究者陸續加入,人數慢慢發展到了現在的80多人。順應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趨勢,馬國賓把群名改成了「大灣區科幻作家群」。這個群裡的科幻作家陳楸帆、科幻研究者三豐也在科幻文學委員會委員名單之列。
吳巖認為深圳是一座具有科幻色彩的城市,而當中最科幻的體現是人,年輕的人們。
他曾經到南科大附屬小學講課,「那些孩子非常了不起,提的各種問題特別專業,還給我寫了好多信。」最近,吳巖就受作家群裡的謝晨之邀,擔任了首屆鯤鵬全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獎的專家評委。
作為鯤鵬獎的發起者與推動者之一,謝晨說,在徵集階段主辦方收到了全國青少年來稿近3萬篇,深圳作為主場,佔了其中的三分之二。「獲獎作品全部是盲評,最後(獲得前三等獎)17篇作品中,深圳市的獲獎作品有8篇。」讓謝晨驚喜的是,其中三等獎一篇作品《人類文明的黃昏》居然出自6年級學生之手。評選出來的作品都要經過論證,保證作品的原創性,對於這一篇,謝晨決定見一見作者呂珈瑤,當面論證。
在老師的陪伴下,第一次見到謝晨的呂珈瑤,顯得很淡定。兩人的交談用去了一節課的時間,從人設的塑造、基於自然科學的基本原理、格言的原創性等多方面的論證中,小姑娘都對答如流。
呂珈瑤就讀於明德實驗學校,喜歡繪畫和閱讀。她的父親從事IT工作,從小就給女兒講歷史、科學故事,後來又把講故事變成了編故事,引導女兒跟自己進行創作接龍。這些故事培養了呂珈瑤創作的興趣,還給她提供了寫作的素材,比如獲獎作品中「虛無之地」的名字,就來源於父女倆編過的故事。
這是呂珈瑤第一次進行小說寫作,花去了她一個暑假的時間,雖然創作中不免遇到挫折,但是她說,獲獎有點在預料之中,「可能是初生牛犢不怕虎吧。」
就憑深圳「後浪」們這股初生牛犢的勁兒,吳巖笑稱,「深圳誕生下一個劉慈欣,是非常有可能的。」
科幻的城市
讓一個搞科幻的人去跨界建築圈和藝術圈結果會怎麼樣?吳巖的答案是,拿它一個獎。
2019年,中國工程院院士、建築師孟建民邀請吳巖、陳楸帆擔任第八屆深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的聯合策展人。這個向來是建築圈與藝術圈翹首以待的大型展覽,在那一年與科幻有了奇妙的碰撞。
當時,吳巖所在的「城市升維」策展團隊在頭腦風暴後,很快形成了以未來市民、城市鍊金師、科幻日常三個部分編制而成的策展理念。但是開始邀請作品時,吳巖的難題來了:一方面他對藝術家不熟悉,無法判斷能找到怎樣的藝術家,更不知道他們的水平在這個領域到底如何;另一方面,他對策展兩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繼續前進。
科幻作家會在策展團隊中逐漸被邊緣化的焦慮控制住了吳巖,他開始退縮轉而去編輯一本談論城市未來的書。這時,另一位策展人王寬給吳巖介紹了中央美術學院的青年藝術家陳娛,她的一番話點醒了吳巖:「為什麼不把書裡的作品交給藝術家,在現實中建構一個同樣的群展呢?」
吳巖被陳娛的熱情所激勵,又變得積極起來,他編輯的這本書《九座城市,萬種未來》,不再是簡單的一本書,更是這一次「城市升維」板塊的特別項目:「九座城市,萬種未來」展覽的靈感來源。他們邀請了9組不同身份的參與者想像未來城市,通過文字、聲音、裝置、場景等多種方式,展現了一組複合型的立體作品,帶給觀眾的是一場進入未來的沉浸式參展體驗。
其中,吳巖創作的短篇小說《九城萬未》,描繪的是人類為了將城市佔地交還給大自然,如何把地球重新變成一個自然星體的探索過程。人們不但找到了這種回歸的方式,還能在一瞬間將全新的城市鋪陳到星球的任何一個未知地方。無數種無法描述的城市形態和未知生物在小說中輪替出現。
藝術家受此故事激發創作了藝術作品 「無名之城」,展現了四組完全屬於未來城市的超級形態,這些形態完全不符合物理學的基本規則,能自由潛入地下、或者急馳到無垠的天空,甚至還能依附其他的生物體內。正契合了吳巖所說的「科幻的核心是想像力的放飛自由」。
最後,這個特別項目獲得了組委會大獎。
「深港雙年展凸顯科幻元素」,也成為了世界華人科幻協會評選的2019年中國科幻十大事件之一。其評語寫道:「這一成功的實踐也證明了科幻作為一種藝術形式和思維方式與城市空間發展、創意設計以及相關領域之間跨界互動的可能性。」
吳巖是科幻作家,是老師,是研究者,但他說,自己不會局限於任何一個身份,他喜歡探索新的領域,並且會盡力創造一個全新的高度,寫小說如此,做科研如此,跨界策展亦如此。他還有很多想要去做的事,比如做常識科幻電影和話劇,比如探索更多跟科技企業良性互動的合作模式,比如摸清想像力到底是什麼,從根上推動科幻文學創作。
「對我來說,我的結局是一個沒有完結的徵程,面向未來的,開放的。」吳巖說道。
吳巖的結局,描繪著深圳的未來。
他們為大灣區科幻助力
馬國賓 深圳長大的80後科幻迷,與一群同樣熱愛科幻的人士共同發起成立了科學與幻想成長基金,中國首支致力於推動科幻產業發展的公益基金。
謝晨 福田校園文學期刊《遇見》的主編。他相信深圳會成為中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的一個高地。
陳楸帆 80後科幻作家。2000年以汕頭市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北大中文系。在校期間,他和同學們成立了北大科幻協會。
三豐 科幻研究者、評論家和活動家,現任深圳科學與幻想成長基金首席研究員。他希望能讓青少年擁有一個科幻的全新思維模式和思維角度。
呂珈瑤 就讀於明德實驗學校六年級,系首屆鯤鵬全國青少年科幻文學獎前三等獎獲獎者中唯一的小學生。▌本文為晶報原創,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來源 | 晶報APP
記者 | 林菲
製圖 | 勾特
編輯 | 李慧芳 李一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