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婚不久的妻子被害案(妻子被害三個月)
2023-06-05 20:45:14 4

一臺冰櫃。

一件雨衣。

一個玻璃瓶。

再尋常不過的東西。
後綴的「殺妻」「刺死女友」等描述,卻讓這尋常,有了讓人汗毛豎立的恐怖血色。
這個月登上熱搜的第三起驚悚案件,終讓我忍不住問到:
她們做錯了什麼?
我們總傾向於把惡性事件解讀為「孤例」「個案」。
但新聞成疊,類似的故事聽得指尖冰涼,意外還會是「意外」嗎?
結構太過類似的敘事裡,必然掩藏著某種共通的規律。
女性安全談過很多,卻很少注意到親密關係裡的女性安全。
今天就來談。
那些被「深情」抵住咽喉的女人們。

讓人心臟停拍的畫面。
本月11日晚,山東萊陽一對母女正常回到家裡。
卻在剛解開門鎖時,被一個身穿雨衣的男子突然鉗住,強行拽進屋內。

來源 | 遼寧衛視《說天下》
留給監控攝像的是一片可怖的死寂。
短短幾秒鐘有太多讓人細思恐極的細節。
其一,這位男子顯然是早早潛伏在樓道內,掐準了時機出手。
是有針對的作案。
其二,身著雨衣證明他知道監控的存在,特意喬裝。
是有規劃的作案。
其三,一次劫走一對母女,又不似在多高檔的小區內。
若不為財,顯然還是有特殊目的的作案。
網友的恐慌,在警方的通報後得到一定緩解。
是孩子親爸,來糾纏前妻要求復婚。

來源 | 萊陽市公安局
有不少人大概鬆了口氣:呼,還好不是無差別害人的性變態。
母女平安的消息,也讓人大呼不幸中的萬幸。

但,我松不出這口氣。
離婚後綁架、強姦,和性變態罪犯又有何區別?
遭受侵害的妻子,可能留下陰影的女兒,又能「平安」到哪裡去呢。
當一個事件從「女性獨居安全」的範疇縮小至所謂「婚姻糾紛」,好像就不那麼讓人人自危了。
可,真的有人能確信,自己不會遇上一段糟糕的關係,一頭身披雨衣的禽獸嗎?
再看一起類似事件。
溫州的一對情侶在街上同行時發生爭吵,男子暴怒中用啤酒瓶將女友當街刺死。

來源 |《一點資訊》
或許是最隨意的場景,最隨意的兇器,最隨意的動機。
但事實是,製造一場橫禍真不需要那麼具體的緣由或周密的計劃。
當然,比起嚇唬大家,我更想探討的是,為什麼同類的事件會一再發生?
或者說,相似的殺心都是如何起意的?
我們可以回頭看看兩樁近乎歷史重演一般的舊聞。
依次在2016年及2021年的兩起殺妻冰櫃藏屍案。
如果你有印象,在兩年前,有一位曾震驚全網的罪犯被處以死刑。
上海殺妻藏屍案的被告人,朱曉東。

來源 |《南方都市報:》
據被告人自己的辯白,他和妻子楊儷萍婚後時有爭吵,二人的矛盾在經歷過一次旅行後被激化到頂點,點火就燃。
悲劇發生在後來的一天早晨。
那天夫妻二人再度因為旅遊期間的問題爭執起來,朱曉東因「不想讓她再說了」,用雙手掐住了楊儷萍的脖子。
直至她失去呼吸。
朱曉東在法庭上自稱是「激情殺人」。
但案件調查過程中逐漸被挖掘出的細節,卻無一能支撐他的說辭。
激情殺人指的是無故意殺人動機,但因失去理智犯罪。
可,朱曉東卻被發現在事發前一個月購買了與殺人相關的書籍,以及一臺用於藏屍的冰櫃。
顯然,他並非臨時動了殺意,冷靜周全的程度更和「激情」二字毫無關係。

來源 |《南方都市報:》
更別說在行兇後當晚,他便支取了妻子的存款,開始了和朋友的狂歡。

來源 |《南方都市報:》
而讓我毛骨悚然的還不止如此。
朱曉東將妻子在冰櫃中藏匿了整整三個月,期間出國旅遊、縱酒享樂,沒受到任何影響。
還會將其他食品一併存放在冰櫃裡。
猶如那不是一具屍體,而就是一塊死肉。
且在這幾十天裡,他一直以楊儷萍的口吻保持著微信的回覆、朋友圈的更新。
包括秀恩愛。

來源 |《南方都市報:》
顯然,這不是一次偶發事件。
而是一次瘋狂且冷血的謀殺。
再說到去年發生在四川蒼溪的另一起案件,手法與這起謀殺竟出奇地相似。
令受害人窒息身亡,後利用冰櫃藏屍數月。
兇手則揮霍玩樂、正常生活,直到東窗事發才開始推鍋給死者。
「這邊也有過錯」「不應該是故意殺人」。

來源 |《九派新聞》
而要論兩起案件最驚人的相似點,還有它們的背景。
女強男弱,女富男窮。
前者是上海獨生女嫁給商場售貨員,後者是網紅主播嫁給地鐵工人。
雖然我從來不會把階級看做愛情的門檻。
但從不多的資料裡你無疑讀得出來,金錢和自尊的缺乏,是他們作案動機的重要來源。

來源 |《九派新聞》
兩名兇手的生活環境如出一轍。
習慣了體面的酒色生活,卻不曾掌握家庭的財政權。
對外逞強,對內無能。
這兩種截然相反的生存狀態形成的張力,拉扯著他們脆弱的自尊心。
因此,一次爭吵,一次羞辱,一次不尊重,足以引爆他們積累已久的怨毒。

來源 |《九派新聞》
男方在家庭的主權被壓制,被控制,直到最後爆發到令他們失去人性。
分析到這裡,你會不會覺得,這兩起命案的發生其實都有跡可循?
我原先也這麼覺得。
但,再轉念細思,我發現這恰恰是最可怕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都如此自然地接受,「父權自尊」受挫,就應該生出惡性事件?
這貌似的「順理成章」,真的有理嗎?

別怪我唐突。
但在如此沉重的社會新聞後,我準備另起話頭,來講一部香港喜劇:
《殺妻二人組》。

分數不高,知名度不大,是鍾鎮濤當年試水做導演的處女作。
讓我多年來印象深刻的,並不是電影本身有多精彩。
而是,它掛著這樣驚悚的一個名字,標榜的卻是「愛情喜劇」。
我想,通過解剖這部爛片,至少能看看,「殺妻」到底是如何發生的。
這種90分鐘的輕體量喜劇其實很不好拍。
最關鍵的,怎麼在最短時間內向觀眾展現核心矛盾?
之於這部電影,是「殺心」從何而起。
男主一號周潤發,在7分28秒就動了惡念。
妻子(王祖賢 飾)向醫生求壯陽藥被他撞見,發哥演的丈夫便以為她出軌的同時還要毒殺親夫。


來源 |《殺妻二人組》下同
想像力何以豐沛至此?
只因為嬌妻平日裡太有異性緣,又愛出風頭,人走到哪裡,哪裡就長出男人堆。

發哥多年來早已是醋罈見底,自尊枯竭。
因而,疑心甚重也是有的。
二號男主B哥的殺心起得略晚。
但到14分26秒,也差不多講明緣由了。
老婆(梅豔芳 飾)嫌他目光短淺,成日裡罵他沒出息。

且,訓夫還不分場合。
當著街坊一群婦孺照罵不誤,鬧得連穿開襠褲的娃兒都知道他窩囊。

兩條劇情線很快收束。
一場酒局上,兩個窩囊男一見如故,飲到爛醉。
兩人一合計,計劃冷不丁地就誕生了。
交換殺妻。

是啊,就這麼簡單。
不需要多誇張的矛盾,酒後失言,就能是一個作案動機。
當然,畢竟這不是羅翔課堂。
酒醒後,兩個男人面對的並非命案,而是大烏龍。
梅姐鬧脾氣住到鄰居家,不在家中。
但發哥和B哥看見滿屋狼藉,能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她死了。
我把你老婆殺了。

進行到這裡,老香港笑片味就很正了。
產生誤會、誤會加劇、解除誤會,我們很習慣的路數了。
但劇情在這裡拋出了一個很詭異的包袱。
B哥對發哥直陳,自己是為兄弟兩肋插刀的人。
他願意陪發哥去坐牢。

發哥問,怎麼陪啊?
他語氣雲淡風輕:殺了你老婆啊。

哈哈哈哈!
太標準的港式黑色幽默了。
但我再回味一會兒,打笑聲裡卻又品到一絲寒意。
二位男主稱這次行動為「捨命陪君子」。

「君子」何來?
他們的答案似乎是,殺掉影響主權的妻子,才成就真男人。
別誤會,我不是要當時光機警察,強行審判誕生於30多年前的一部糊片的意識形態。
《殺妻二人組》確實只是一部胡鬧殺人、賣力搞笑的電影。
發哥與B哥在別墅布下天羅地網。
聚焦煤氣管道的透鏡。

漏電的大電視。

泳池裡的食人魚。

還有更深思熟慮的,殺人不留兇器的冰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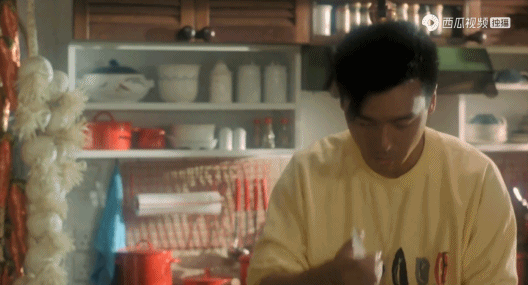
而閉眼都能預想劇情走向是,這些陷阱最後全報應在自己身上了。
整個過程足以讓人捧腹大笑。

但,作為一個靠批評影視作品吃飯的人,除了笑果,我總還想深挖到邏輯層面。
還是前文那個問題:為什麼順理成章?
窩囊廢的反殺,妻管嚴的爆發,對我們來說似乎完全在意料之中。
電影只需花上幾分鐘展現男主在家庭中的弱勢形象,我們就會覺得,嗯,他選擇殺妻是邏輯順暢的事情。
這好像是在默認,丈夫的確有一種對自尊的絕對需求。
以至為了守護它,他們做出再殘酷嗜血的事情,也在我們能理解的範疇中。
且,最後也能在深情與浪漫中被原諒。

這部陳年「愛情喜劇」,在我這裡開始趨近於現實主義恐怖片。
精神分析學有個比方叫「弒父情結」。
每個人都會本能反抗控制自己的父權權威,以實現自我的獨立。
而無論新聞或電影裡。
我發現,或許還有一種走向扭曲的「殺妻情結」。

前文提到了,B哥的老婆愛嘮叨。
平日最常教訓他的一句話就是,胸無大志。

而貫穿了全片的這四個字,在最後有個讓我不寒而慄的復現。
在殺妻計劃開啟後,兩位男主角也開始了癲狂的較量,看誰想出的殺人手法更毒辣。
獲勝的竟然是平日唯唯諾諾的B哥。
他搞出來的「腰斬陷阱」,把計劃提出者發哥都嚇到想叫停。

這時,B哥終於露出了宛如贏得全世界的微笑。
夠大志了吧

你懂這種恐怖嗎?
在長時間的壓抑下,他居然已經把殘忍當成了一種英雄主義。
而這,大概也是那麼多「殺妻」事件中,一種共通的心理。
我們甚至可以更「理中客」地來談這種畸形兩性關係。
畢竟並非當事人,不好草率把一段失敗感情隨便歸罪到某一方身上。
僅從電影裡看,兩位女主角有沒有問題?
或許有。
她們犯的「錯」大概是,強勢而不自知。
梅姐是服裝設計師,有一份更穩定長遠的事業。
且作為直球的事業女性,她在習慣性忽略老公的自尊心。

老王沒啥特長。
就是長得有點驚為天人。
且當慣了全體直男的視覺中心,她也會不自覺忽略老公的安全感。

但問題是,地位不對等不是任何一方的錯誤,而是雙方配置的問題。
但我們所看到的,丈夫們的解決措施是什麼呢?
不是提升自己來平衡地位。
而只有無能暴怒。

他們的「殺妻情結」起於在婚姻中被掌控的挫折感。
這種挫折感本是人之常情。
但問題是,丈夫們想要的並不是平等,而是反過來掌控強勢的妻子。
又實在羸弱到沒有這種能力。
於是,只能通過殺死讓自己不體面的妻子,來重獲自尊。
在翻找「蒼溪藏屍案」的資料時,我在死者母親的表述中找到了印證這一想法的表述。

來源 |《九派新聞》
但,「殺妻情結」絕不只誕生在一種模式裡。
來複習一個與上述案例不大類似,但也是在世界範圍內最知名的殺妻事件。
辛普森案。
應該不少人對這件往事耳熟能詳:美國傳奇橄欖球運動員O.J.辛普森被指控謀殺前妻妮可,在證據鏈對自己極度不利的情況下,靠最頂級的律師團隊力挽狂瀾,成功脫罪。
對於此案,人們通常聚焦於「程序正義」「種族矛盾」「政治正確」等宏大概念。
但我只想聊回這對夫妻本身。
辛普森是個徹頭徹尾的控制狂。
他僱人監視妻子,在她身邊安插奸細,甚至常常在妻子獨自出行時親自跟蹤。
這種控制癖直到二人離婚後,都沒有結束。

來源 |《辛普森:美國製造》下同
而讓這個男人最終走向瘋狂的,是前妻的最後通牒。
她不再需要辛普森了。

在兩人徹底一刀兩斷後不到一個月,妮可的屍體被發現躺在一棟豪宅門口,她的喉嚨被利器割斷,鮮血遍灑現場。
而隨後在辛普森住宅門口,警員們找到了一輛白色轎車,其門把手上沾著明顯的血跡。

辛普森與妮可不是典型的「女強男弱」。
辛普森是國民級的巨星,是那個年代極少數能在上流社會如魚得水的黑人,而妮可只是一個當服務生的二代移民。
但,兩個人的生活經歷卻拉開了他們精神上的距離。
O.J.出生於黑人貧民窟。
從小所受到的歧視和排擠,讓他在功成名就後只學會了一件事。
扮演白人。

他試圖讓全世界忘記他的膚色和出身,竭盡全力維持著生活的體面和尊嚴。
因為曾經一窮二白,所以他太貪婪於此刻擁有的一切,恨不得像史矛革一樣把一切都用烈焰守住。
妮可自然也被他視為財產之一。
但,需要強撐出的「自尊」,本就是「自卑」的同義詞。
在面對倔強的妮可時,施暴狂辛普森其實軟弱到只能動用暴力。
妮可的摯友多年後回憶道,她骨子裡有一種讓辛普森無法掌控的不馴。
而這既是妮可的迷人之處,也是她的死因。

辛普森的羸弱不在於地位、階級、膚色。
而是與許許多多的殺妻者一樣的,一種因自卑誘發的人格缺陷。
這或許能給我們在戀愛、擇偶上提個很必要的醒。
說回《殺妻二人組》。
整部雞飛狗跳的電影有一枚鏡頭深得我心。
兩位妻子駕著車,帶著憤怒與悲哀,在暮色中遠去。

雖然她們沒有逃過命定的大團圓結局。
但,此刻自由的姿態卻美得讓人失魂。
同電影的結局一樣,我們文化語境裡一直有種深刻的,對圓滿的追求。
要讓親密關係長久、平和、波瀾不驚。
而為了穩定,人們又在不斷勸導女性忍讓、壓抑、縱容、原諒。
但,請別再相信任何有關親密關係的謊言。
不要相信一根刺,是因為自己不夠包容或太過包容,而變成一把殺人刀。
罪惡歸根結底,是因為兇徒心中有刀。
不要寄希望於一段有毒的關係。
任何形式的愛中,唯一真實的,就是自己的感受。
去做一個自由的,隨時有勇氣出逃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