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電影女性形象(張藝謀電影女主不僅矮山根)
2023-06-09 23:39:52 2
說起張藝謀的美學,大家最先想到的,除了他電影裡繽紛濃烈的色彩。


大概還有歷任謀女郎中常見的矮山根、寬眼距,也就是所謂的「鯰魚臉」。
無論是鼎鼎大名的鞏俐、倪妮、周冬雨:


還是半紅不火的張慧雯、劉浩存:

以及短暫亮相之後就「查無此人」的李曼:
國師對於矮山根、寬眼距、中小眼的偏愛,貫穿了他三十多年的職業導演生涯。
不過除了色彩和鯰魚臉,張藝謀還有一個很少被人提到的,隱藏的審美執念,那就是——舞者出身。
眾所周知,章子怡八歲開始跳舞,十一歲時考入北京舞蹈學院附中。在十七歲進入中戲學習表演之前,扎紮實實跳了整整九年的民間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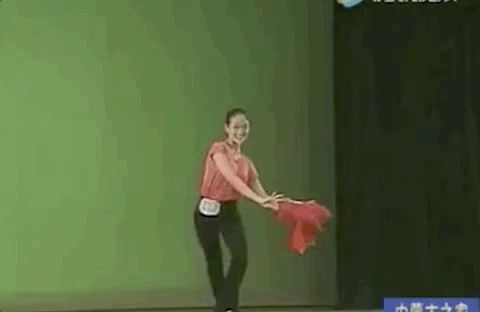
董潔在出演《幸福時光》和《金粉世家》之前,最為大眾所知的,也是她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的舞者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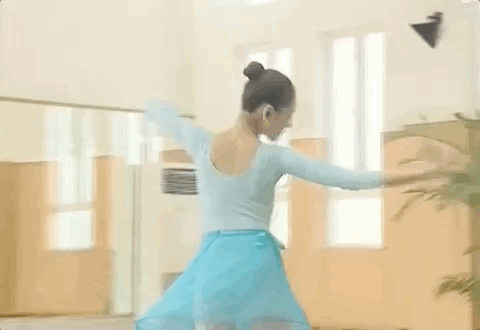
倪妮的舞者背景,雖然不及章子怡和董潔那樣硬核,但依舊有拿得出手的成績。比如她在南京傳媒學院求學期間,就拿到過江蘇省的國標舞冠軍。

至於在《歸來》裡扮演丹丹的張慧雯,本身就是北京舞蹈學院民族民間舞專業的學生。

去年發了一堆通稿,試水美人人設的劉浩存,更有說服力的營銷點,其實也是她北舞藝考第一名的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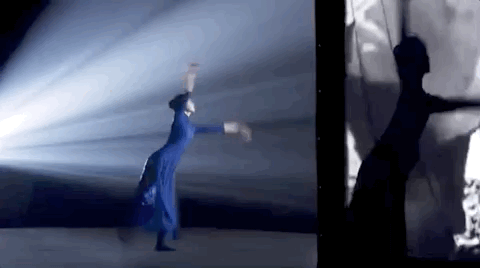
幾乎可以這樣說,大家叫得上名字的「謀女郎」,除了鞏俐和《一個都不能少》裡的魏敏芝,其他都是專業/準專業舞蹈演員。張藝謀對於舞者的偏愛,可見一斑。
究其原因,除了像張藝謀的老搭檔張偉平說得,「舞蹈演員特別能吃苦(可期待的敬業程度更高、更易合作)」之外。首當其衝的必然是舞蹈演員的外型,特別是她們極具表現力的身體。

這一方面跟張藝謀的視覺語言風格有關。我們可以發現,張藝謀很喜歡用大全景以及精細調度的遠景長鏡頭,來組織敘事。

在這樣空曠且節奏明快的視覺環境中,演員的身體在塑造角色時,相對於臺詞和面部表情,就變得尤為重要。
她的行走、奔跑、跳躍,必須具有足夠的表現力,才能保證與視覺背景在節奏感上的協調,讓觀眾不出戲。

像範冰冰這樣四肢分離(核心力量弱)、看上去懶懶散散的身體,自然無法滿足這樣的拍攝需求。

另一方面,身體本身,其實跟聲音、色彩一樣,也是一種藝術表達的媒介。
越是優秀的導演,越能超越對臺詞和布景的迷戀(說得就是某些話癆電影和壁紙電影),把許多精力放在更隱微的部分,比如對角色身體的表現之上。
王家衛鍾愛的張曼玉,姜文鍾愛的周韻,都是應用身體語言的高手。


從這個角度來講,接受過舞蹈訓練的身體,在電影中即便不跳舞。也會通過行走坐臥的細節,「潤物細無聲」地豐富我們的審美體驗,以此為電影本身增加魅力。
比如劉浩存在電影《一秒鐘》中裡的這段看似「平平無奇」卻傳神的追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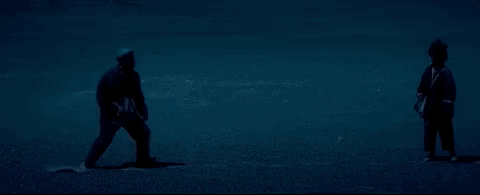
髖部斜傾、腿在跑,頭肩部卻成反方向回望。這一連串動作,所要求的腰部、肩頸柔韌度以及核心控制力是很高的。
光是轉頭的同時保持沉肩,沒有經過相關訓練的人就很難做到。
我們再來看這段跑戲:

劉浩存不僅是在往前跑,還有一絲彈跳的輕盈感,四肢是在空氣中有節奏地擺動,而非機械地移動位置。
她動了,空氣也動了,畫面的節奏也變得更加明快。與跟她搭戲的張譯,這種簡單直接「向前衝」的普通人運動員式跑法,非常不同:

還有這個被甩出去之後,找平衡的一連串動作:

倉皇但並沒有徹底失去控制的狼狽,非常具有舞蹈「欲左先右」的韻律感,身輕體柔但並不是沒有力量。這是身體舒展同時又很有控制力的人,才能給予我們的觀感。
還有這個躲避自行車的微小動作:

她是下意識地踮起腳整體向後「跳」,而不是普通人笨拙尷尬地「挪」。
早熟少女的機敏氣質,就是通過這些細節,傳遞給了觀眾,而不是流於表面的歪頭嘟嘴。美學表達自然又有力,因此顯得非常高級。
看到這裡,對於國師為何偏愛舞蹈演員,相信大家心裡已經有了答案。

那麼為什麼舞者的身體比起素人更具表現力呢,其最根本的原因在於:
身體開發程度的不同(學過舞蹈只是表象)。
每個人天生都擁有一個身體,但我們對於身體的了解程度、應用程度以及控制水平卻是千差萬別。

舞者通過專業的舞蹈學習,不但知道「好看的動法」,並且習慣了那樣動。舞蹈教育也鼓勵舞者去探索自己的身體,通過身體表達自己的思想情感。
但素人從小到大接受到的身體教育,通常只有規訓而沒有表現,表現力差自然就變成了必然的事。

回望我們的成長過程,可以發現其中充滿了對身體的馴化。早在幼兒園時期,老師就要求我們上課時要坐得端端正正且目不斜視。
那些按照自己舒服的節奏來,歪歪扭扭不配合的小朋友,則會受到老師和家長的批評。

從小學開始直到高中畢業,我們有12年(至少三千多天),需要在規定的時間內,安安靜靜地坐在教室裡。
那些無法做到的孩子,則會被教育制度拋棄。

可是想想看,就像貓咪本能地需要伸懶腰、追逐奔跑以及攀爬跳躍一樣。人作為一種動物,也必然有他天然的動靜節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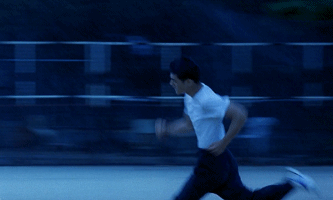
然而這些節奏在後天,普遍都受到了極大的壓抑。
身體被當成了精神和思想的奴隸,它的每一次活動,似乎都需要思想給它一個外在的理由,比如「強身健體才能好好工作/學習」、「身體好才能做更多的事」、「學個舞蹈身材好」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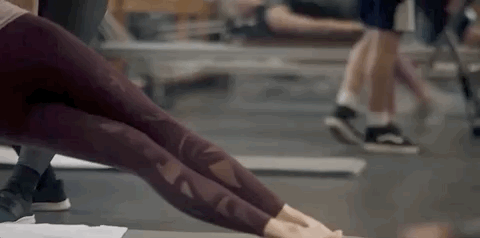
除此之外,一個人似乎理應就是靜止不動的。
然而在舞者、特別是研習現當代舞的舞者身上,我們卻可以看到那些,久違了的,屬於人類身體的天然律動,那些「身體動是因為它想動」的結果。

讓我們發現。原來翻滾、轉圈、跳躍,本來就是我們身體需要的東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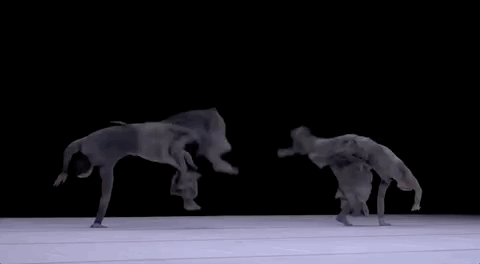
原來在社會規訓的身體之下,我們還有一個自然的身體。「動」是這個身體本身的渴望,「靜止」才需要理由。

當看到舞者在稻粒構成的瀑布中快速旋轉的時候,我們似乎很難找到一個除了「爽」之外的詞語,去形容這種感受。身體就這樣用它自己的方式,打動了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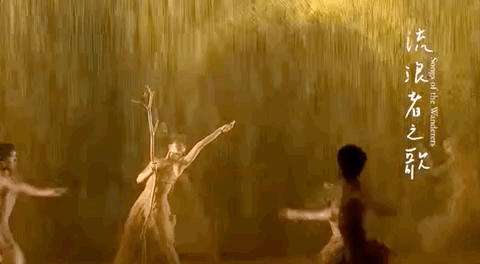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脫離了精神和思想控制之後的身體,似乎真正擁有某種精神之美。
她們是中性的,強健的,也是篤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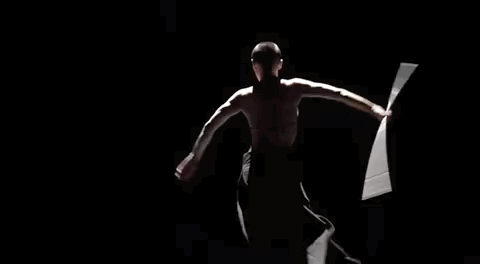
無論是高是低、是男是女,手腕是否過襠、頭肩比是否大於1.5,都讓我們感受到了那份由內而外的力量感。
那份覺知身體、自我和解之後,所呈現得生命本身的尊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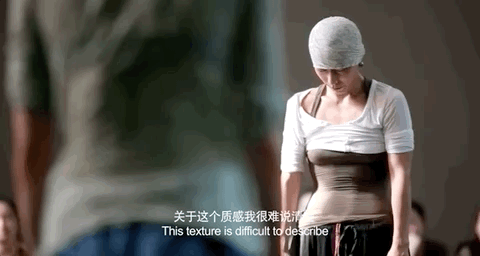
或許這也是為什麼相對於健身房身材,我們總會更容易欣賞舞蹈身材的原因。
前者的基礎在於解剖學及人體工程學,練哪、怎麼練都需要成套的人體醫學做支撐。以此塑造出來的身體,本身即具有一定的「人造感」。

相對於那些由「自動自發」的舞蹈,所塑造出來的身體,在自然及精神之美的維度,也就要遜色一些。

總之,大概沒有任何一個東西會像身體一樣,離我們這麼近,卻又讓我們對它如此陌生。
美作為一種生命願望,得以在舞者的身體之上,呈現出最具體的樣貌。那些無拘無束順從內心的奔跑、跳躍,是舞者,同時也是理想中的我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