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結局解析(跪求這電影結局別翻車)
2023-06-20 14:50:58 1
14年後,孫海洋夫婦終於又一次擁抱到了自己的孩子。
他們永無止境的尋找和等待,在那一刻似乎有了盡頭。

電影《親愛的》原型人物孫海洋夫婦
張譯、黃渤等出演過《親愛的》電影的演員,也紛紛淚奔祝賀。

看起來,一部留有遺憾的電影終於續上了圓滿結局。
但其實,現實中罪惡與情感的纏鬥,仍看得人揪心。
那些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有多少能在現實世界響起回聲?又有多少能鼓勵人們笑中帶淚永不言棄?
不如,今天就從《親愛的》說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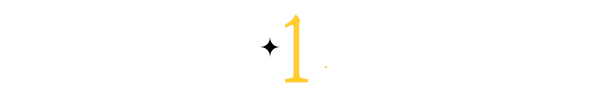
《親愛的》裡張譯飾演的韓德忠,原型正是孫海洋。
一個組織起尋親互助團體的富商。
他是找尋那些失蹤孩子們的家長中,最積極最堅定的代表。

可同時,韓德忠也代表著現實裡的大部分——他找不到,找不動了。
當這個人選擇「倒戈」時,電影與現實生活的界限不再明晰。

在找孩子的漫漫長路上,命運給韓德忠開了一個又一個的玩笑,讓他不得不信命、信佛。
他曾殘忍地生吃猴腦,後來丟了孩子,從此只吃素不吃肉。

追趕疑似拐賣孩子的貨車,拼命搶下麻袋一看,裡面是只猴子。
那一刻,他只能在雨中絕望地抱頭痛哭。
你要讓他怎麼不信命。

我不敢去想,有多少被拐孩子的父母,是否也有過這樣的心情——這是不是我的報應。
《親愛的》裡另一位家長原型彭高峰就有過這樣的恐懼。
他害怕與人發生爭執,怕聽到這樣的話——
「你上輩子做多大的缺德事啊,孩子被你搞丟了。」
幸好,電影裡的遺憾在現實中暫且畫上了一個句號。
孫海洋夫婦終於可以停下腳步,享受十幾年來第一次平靜的喘息。
事實上,這幾天關於這對父母和他們尋回的孩子的紛紛擾擾,一直沒停過。
這也在無形中創造了更多的討論空間:
有博主科普防止兒童拐賣的知識,分享「團圓」小程序,關注團圓行動;也有人提倡給孩子和父母都提供心理諮詢服務;還有人在各大平臺針對「買賣是否同罪「的議題發表觀點……
當絕大多數人能秉承著這樣的信念發聲——找到一個是一個,少丟一個是一個,那麼,真正的團圓應該會近一點吧。


扎因把父母告上了法庭。
為什麼?
因為生了他。

電影《何以為家》改編自敘利亞難民兒童贊恩的真實經歷。
無數個與扎因、贊恩一樣的孩子,他們不長的生命裡受到的苦難,大多直接來源於父母。
他們生活在什麼樣的家庭裡?
生、生、生,不停地生,男女各有各的用處。

扎因12歲,他的一天是到惡棍房東的小賣部打零工,再到街上攔路人賣果飲。
為了賺一些零錢在街頭遊蕩,回家再被父母謾罵毆打。
上學,是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薩哈,扎因11歲的妹妹,被穿上粉色裙子和中年房東「相親」。
扎因像應激的小獸拼死想留住妹妹,而怕被收回房子的父親噤若寒蟬。
最後,薩哈死於小產。

扎因的父母有罪,但他們不是惡的源頭。
無數個小家庭駭人聽聞的悲劇,背後是整個社會的滿目瘡痍。

《何以為家》,直譯名《迦百農》,阿拉伯語中指代著混亂和災難。
這正對應著黎巴嫩,這個巴以衝突間接受害者的複雜國情。
無數難民湧入,黎巴嫩的人口由四百多萬本國居民和幾十萬巴勒斯坦難民、上百萬敘利亞難民構成。
這些難民擠在不屬於他們的城市的偏僻角落,苟且偷生。

當活著成為唯一的目的,不會再有人去思考尊嚴、暢想未來。
多生一個,多一個勞動力,多一份資源,是這些父母能想到的最好方法。
理所當然地,兒童,作為最弱勢的群體,成為了被剝削的最後一個環節。

非法買賣、非法僱傭、童婚、毒品、性侵……他們的世界遍布危險。
導演拉巴基用最直白乾脆的鏡頭,還原了黎巴嫩街頭最常見的景象。
孩子們衣著破爛,滿嘴髒話,吞雲吐霧,他們早就被這個世界異化。
拉巴基的本心,也只是想讓藍天白雲下的我們看見,原來還有孩子,在這麼活著。

導演拉巴基說:
「我不想天真地說電影可以改變世界,但如果它可以改變你看待這些孩子的態度、或是你看待你自己生活的態度,那麼它至少可以一定程度地改變你。當千千萬萬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視角看待這些問題時,真正的改變才會開始發生。」
直至今日,拉巴基仍與政府密切合作,解決更多難民小孩的問題,並想通過紀錄片的形式讓大家看到現實正在好轉。
贊恩是不幸的,也是幸運的。
《何以為家》播出之後,贊恩和家人在聯合國難民署的幫助下移民挪威。
他滿足了自己的小小願望,有了屬於自己的床,睡到了自己的枕頭。

而難民營裡還有無數個贊恩和薩哈,他們生活在無知、愚昧、骯髒的世界。
當成年人引發的戰爭,後果波及到每一個無辜的孩子身上,那些人是否需要反思、是否嘗試停止?
幸好《何以為家》在,贊恩就一直在吶喊——
你們是否可以停手,留給我一個乾淨的世界。


真實故事改編的電影,自然繞不開鼎鼎大名的《熔爐》。
電影裡,姜仁浩為了孩子與社會的陰暗面對抗,在荊棘路上孤獨長跑。

現實裡,《熔爐》能夠上映,則是無數人跨越6年不停歇的接力。
2005年,全應燮老師,姜仁浩的原型,第一個揭開了光州仁化學校的醜惡。
自 2000 年起,以校長、教務主任金氏兄弟為首,仁化學校的數位教職人員對學生進行施暴和性侵。
受害者年齡從 7 歲到 20 歲,性別有男有女。

校方威逼利誘,用各種手段讓證人閉嘴,讓受害孩子的父母籤下和解協議書。
根據韓國《未成年性行為保護法》規定,受害者與施害者達成和解,法律也無法繼續介入。
二審判決,校長和教導主任被判緩刑獲釋。
而全應燮老師丟了工作,沒了收入再度陷入貧困。

所幸,他將第二棒遞到了另一個人手中——
韓國作家孔枝泳,她被稱為韓國文學的自尊心。
在新聞上看到關於仁化學校報導,孔枝泳坐不住也忍不住了,她立馬動身去往光州。

與孩子們相處的十天裡,孔枝泳小心翼翼,怕自己的一句話一個動作就會對孩子們造成二次傷害。
終於,這個溫和又堅定的女人得到了孩子的信任,聽到孩子們說道「無論男孩女孩都遭受了性侵害、不分對象的毆打虐待」後,孔枝泳開始用筆對黑暗宣戰。

創作《熔爐》小說的過程是煎熬的,孔泳枝因為壓力過大時常發燒,還需應對校方找上門來的威脅。
兩年半後,《熔爐》小說面世,創下當時韓國網絡文學的連載點擊紀錄。
自此,第三棒也順利交到了《熔爐》小說的讀者孔劉手中。

作家做了作家的事,演員孔劉也想做些演員該做的事——將《熔爐》影視化。
為了自己,也為了無辜的孩子,他無法做到視而不見。
「我也不知道自己會幹演員這行多久,等我的年紀再大一些,回顧我曾參與作品列表的時候,希望有一部《熔爐》這樣的作品。」

2011年9月22日,電影《熔爐》在韓國首映,創下觀影人次570萬的記錄,約佔韓國人口的十分之一。
最終,衝向終點的這一棒,交到了全體韓國民眾的手中。
上百萬人在韓國門戶網站Daum上發起請願。
2011年10月,韓國國會208名出席會議的議員以207票贊成,1票棄權的結果通過了《性暴力犯罪處罰特別法部分修訂法律案》,又名「熔爐法」。
這是世界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電影名命名的法律。
《熔爐》改變了世界。

電影,從不僅僅是電影,它是一種有能量的媒介。
導演楊德昌說電影延長了我們人生至少三倍。
在一個個或貼近現實或放飛想像的世界裡,我們看到了不同人的際遇、不同地點的風貌、不同文化的風情,看到了生活之外更大、更廣闊的世界。
看到了我們也許一輩子不會碰觸的生命的角落。
《我不是藥神》以抗癌藥代購第一人陸勇的原型,是小人物的大愛。

《籠民》再現香港底層民眾的居住問題,是階級的固化和壓迫。

《弱點》講述白人家庭收養黑人男孩,是善意終將有回報。

......
電影是生活某一面的聚焦。
在其中,生命延長的不僅是時間,更是感受、是體驗、是視角。
我們潛移默化中被感染、被鼓舞、被塑造,願意為不幸惋惜,為不公發聲。
電影的傳播從不局限在影院。
當它在現實裡震蕩出漣漪時,才在某種程度上真正被看見、被看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