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新石器時代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
2023-08-13 17:50:53 1
河北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一、引 言什麼是植物考古?植物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屬於科技考古範疇①植物考古通過田野考古發掘發現和獲取考古遺址中埋藏的植物遺存,然後在實驗室整理和鑑定出土的植物遺存,分析和認識出土植物種屬與人類生活的相互關係,達到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和解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考古學研究目的我們都知道,人類與植物的關係密不可分,衣食住行都離不開植物,特別是在古代,植物是人類最重要的基本生活資料,所以為了達到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這個現代考古學的研究目的,考古學必須依靠植物考古的參與,植物考古成為現代考古研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科技考古領域之一植物考古的研究內容涉及的學術問題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業起源問題,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於河北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我們一起去了解並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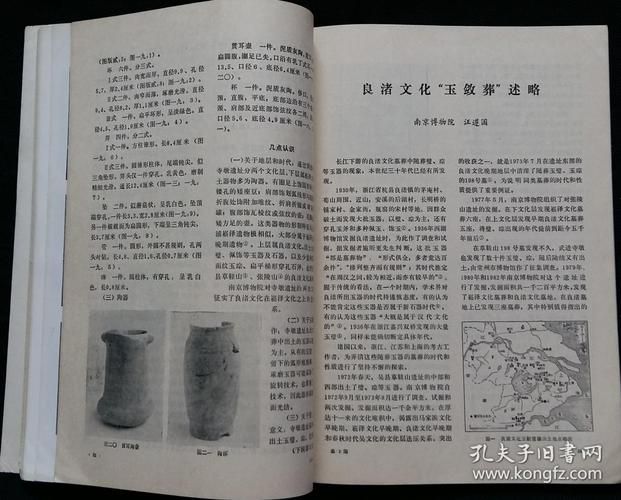
河北新石器時代農業考古概述
一、引 言
什麼是植物考古?植物考古是考古學的一個研究領域,屬於科技考古範疇①。植物考古通過田野考古發掘發現和獲取考古遺址中埋藏的植物遺存,然後在實驗室整理和鑑定出土的植物遺存,分析和認識出土植物種屬與人類生活的相互關係,達到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和解釋人類社會發展過程的考古學研究目的。我們都知道,人類與植物的關係密不可分,衣食住行都離不開植物,特別是在古代,植物是人類最重要的基本生活資料,所以為了達到復原古代人類生活方式這個現代考古學的研究目的,考古學必須依靠植物考古的參與,植物考古成為現代考古研究中應用最為廣泛的科技考古領域之一。植物考古的研究內容涉及的學術問題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農業起源問題。
為什麼說「農業起源」是植物考古最重要的研究內容?首先,農業起源是整個考古學研究的熱門課題之一。我常說,現代考古學的研究內容集中在三大起源問題上,即人類起源、農業起源、文明起源。這個說法自然有些片面或簡單化,但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現代考古研究的主要問題,如果仔細思考,或多或少都與這三大起源相關聯。其次,在考古學所有的研究領域中,植物考古與農業起源研究的關係最為密切。農業是指人類利用植物和動物的生長發育過程獲取生活資源的生產行為,廣義的農業就是所謂第一產業,包括以自然生物為生產對象的所有產業,例如種植業、畜牧業、林業、漁業等;狹義的農業僅包括種植業和由種植業提供飼料來源的家畜飼養業。農業起源研究涉及的是狹義的農業,狹義農業的核心是種植業,種植的對象是植物,所以最能反映古代農業起源過程的實物證據應該就是通過考古發掘出土的植物遺存。因此說,農業起源研究離不開植物考古的參與,植物考古是探討農業起源的最為有效的考古研究手段。
植物考古與其他考古學研究領域的主要區別在於研究對象,植物考古的研究對象是考古發現的與古代人類生活直接或間接相關的植物遺存。所謂直接相關就是指那些被人類利用的植物,包括食物、燃料、材料、工具、用具等;所謂間接相關是指那些雖然對人類沒有利用價值,但卻間接地影響到人類生活的植物,比如依附在人工生境的各種雜草。通過考古發掘可以發現的古代植物遺存分為植物大遺存和植物微小遺存,植物大遺存是指那些用肉眼或低倍顯微鏡就可以看到的考古出土植物遺存,例如通過浮選法獲取的炭化植物遺存、特殊保存條件下的非炭化植物遺存,以及木材碎塊和炭化木屑。植物微小遺存是指那些必須通過高倍顯微鏡才可看見的埋藏在考古遺址文化堆積中的植物遺存,包括孢粉、植矽體和澱粉粒。孢粉是指無性繁殖類植物的孢子和有性繁殖類植物的花粉,植矽體是植物在生長過程中吸收土壤中的液態矽並充填到細胞和組織中而形成的固態矽化物,澱粉粒是植物的儲藏細胞②。
考古出土植物遺存中最常見、也是最重要的是通過浮選法獲取的炭化植物遺存。由於人類的生活離不開火,所以考古遺址文化堆積中埋藏有大量的經過火的洗禮被炭化的植物遺骸,炭化作用使得有機質的植物轉變為能夠長期保存的無機質的炭化物質。炭化物質的相對密度低,小於1,水的密度是1,一般土壤顆粒的密度是2.65,據此,考古學者創造了「浮選法」用以獲取遺址中埋藏的炭化植物遺存。浮選法的工作原理和操作方法非常簡單,伴隨考古發掘,在選定區域或遺蹟單位採集土樣,然後將土樣放入水中,比水輕的炭化物質漂浮在水面,比水重的土壤顆粒沉入水底,這樣就可以使得炭化植物遺存和土壤分離,從而提取之③。由於浮選法簡單易行,獲取的炭化植物遺存出土背景明確,出土植物遺存特別是植物種子的植物種屬鑑定準確,相應的量化分析方法科學有效,因此浮選法成了植物考古最為重要的一種獲取和研究手段。我們今天要介紹的就是通過浮選法在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獲取的植物遺存。
什麼是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是一個考古學的時間概念,一般按照所謂三大要素界定新石器時代,即磨製石器、陶器製作、原始農業(種植業和家畜飼養業)。但是,越來越多的考古發現揭示,這三大要素是否能夠作為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誌值得重新考慮。
先說磨製石器。究竟什麼是「磨製石器」就值得討論,石器通體被磨光還是僅局部被磨光?如果按照通體磨光來定義磨製石器的話,石器表面磨光區域覆蓋到什麼程度才能被稱為通體磨光?根據考古發現,通體完全被磨光的石器實際出現得很晚,大約在新石器時代中期。如果按照局部磨光定義磨製石器的話,有些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也出土有局部磨光石器的例證,例如在陝西宜川龍王辿遺址出土的舊石器時代末期石器中就發現了一件刃部磨光的大石鏟④。另據國外報導,澳大利亞的一處舊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了距今6.5萬年前的磨刃石器⑤。由此可見,不論通體磨光還是局部磨光,磨製石器與新石器時代的開始關係不大。
再說陶器製作。考古發現揭示,東亞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已經出現了原始陶器,例如日本繩紋時代的早期陶器年代最早可達距今1.65萬年⑥,在中國南方地區發現的一系列舊石器時代末期至新石器時代初期的洞穴遺址中,很多都曾出土過距今1萬年以前的陶器⑦。最新研究還發現,江西萬年仙人洞遺址出土陶片的14C測定年代甚至達到了距今2萬年前⑧。但是,與東亞地區完全相反的是,西亞地區在栽培作物和家養動物出現後的一個很長時間段內,當地古代先民仍然沒有掌握陶器製作技術。所以西亞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期被稱作「前陶新石器時代」。這說明,陶器的出現也不能作為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誌。
相比較之下,原始農業作為新石器時代界定的要素比較靠譜。事實上,著名考古學家柴爾德提出的「新石器時代革命」的主要內容就是原始農業的出現,以及由此形成的定居生活。目前世界各國的考古學界大多數也是以原始農業的出現作為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標誌,例如前面談到的西亞「前陶新石器時代」就是以栽培作物和家養動物的出現作為標誌。
考古發現證實,現今世界上的主要栽培作物和家養動物的馴化時間大多數起始於距今1萬年前後,例如起源於中國的水稻、粟和黍兩種小米,以及家豬等,這與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全球氣候變化直接關聯,所以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起始年代也被確定在距今1萬年前後。考古學界普遍認為,距今3800年前後的二里頭文化時期是中國青銅時代的正式開始,所以在其之前的距今4000年前後的龍山時代應該是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最後一個階段。據此,中國的新石器時代的絕對年代應該在距今1萬年前後至距今4000年前後之間。
在歷經數千年的新石器時代進程中,中國廣大區域內分布著幾個並行發展的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例如,西遼河上遊地區的紅山文化序列,黃河下遊或海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序列,黃河中遊地區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序列,黃河上遊或西北地區的馬家窯文化/齊家文化序列,長江下遊地區的良渚文化序列,長江中遊地區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序列,長江上遊或成都平原的寶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序列。下面我們將按照這些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分別介紹我國新石器時代的植物考古發現。
二、西遼河上遊地區
西遼河上遊地區是指以西拉木倫河和老哈河為主的西遼河源頭流域地區,在行政區劃上以內蒙古赤峰地區為主,同時還包括了通遼地區西部和遼寧朝陽地區北部。西遼河上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相對比較單純,最早的是小河西文化,絕對年代在距今9000-8500年間,其後順序為興隆窪文化(距今8000年前後)、趙寶溝文化(距今7200-6400年)、紅山文化(距今6500-5000年)、小河沿文化(距今5000-4000年)和夏家店下層文化(距今4000-3600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紅山文化。
西遼河上遊地區的植物考古工作比較系統,21世紀以來在該地區進行的考古發掘項目幾乎都開展了浮選工作,其中以赤峰學院植物考古實驗室的工作最為突出。根據不完全統計,在各種學術刊物上已經發表浮選報告的西遼河上遊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近10處。
由於已經發現的小河西文化時期的考古遺址數量有限,而且其中多數是在20世紀進行的考古發掘,而浮選法21世紀初才在國內考古學界逐步普及開來,所以目前尚無機會在小河西文化遺址開展系統浮選工作。
興隆窪文化時期的植物考古以興隆溝遺址的最為重要。興隆溝遺址位於赤峰敖漢旗,包括三個地點,分別屬於興隆窪文化(第一地點)、紅山文化(第二地點)和夏家店下層文化(第三地點)。伴隨2001年的考古發掘,在興隆溝遺址三個地點都開展了浮選工作,合計共採集浮選土樣1500餘份,這是迄今為止國內考古學界開展過的規模最大的浮選工作。從興隆溝遺址浮選結果中出土了大量的炭化植物遺存,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第一地點的發現。
興隆溝遺址第一地點是一處興隆窪文化時期的大型村落遺址,浮選出土了炭化黍粒和粟粒兩種小米遺存,共計1400餘粒,其中絕大多數是黍粒,粟粒的數量較少⑨。出土的炭化黍粒呈長圓形,形態特徵和尺寸大小明顯有別於野生的黍屬植物種子,但與現代黍粒也略有不同。粟和黍這兩種小米在其馴化過程中籽粒的進化趨向應該是逐漸由小變大、由長變圓、由癟扁變豐滿。據此判斷,興隆溝遺址出土的黍應該處在由野生向栽培的馴化過程之中。出土炭化黍粒被分別送往中國、日本和加拿大的14C年代實驗室進行加速器質譜(AMS)年代測定,三個實驗室的測定結果幾乎完全一致,出土黍粒的絕對年代為距今7650年。直至今日,興隆溝遺址出土炭化黍粒仍然是已知的考古出土的具有直接測年數據的年代最早的栽培小米,這一重要發現為探討黍的馴化以及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實物資料和信息。
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是一處紅山文化遺址,由於文化堆積埋藏較淺,大多數遺蹟現象已經被現代農田破壞,可供採集浮選土樣的堆積單位有限,所以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比較貧乏,但從中還是發現了少量的炭化黍粒和粟粒。興隆溝遺址第二地點還浮選出土了一些堅果或核果遺存,包括橡子、榛子、山核桃、山杏、歐李等。相同情況也出現在其他紅山文化遺址的浮選結果中,如赤峰紅山區的魏家窩鋪遺址,文化堆積埋藏得也很淺,雖然發現的紅山文化時期房址數量很多,但大多數僅剩房基,可供採集浮選土樣的文化層較薄,因此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並不豐富,出土植物種子不足百粒,其中包括炭化粟33粒和黍16粒⑩。相比較而言,哈民忙哈遺址的浮選結果最為豐富。哈民忙哈是一處紅山文化村落遺址,位於通遼科左中旗,伴隨考古發掘採集了44份土樣,浮選出土了80萬餘粒炭化植物種子,但其中的絕大多數(99.9%)是大籽蒿種子,其他植物種子合計僅710粒,其中包括黍(615粒)、粟(20粒)和大麻(3粒)三種農作物籽粒(11)。大籽蒿是一種可食用的草籽,現在流行於西北地區的「蒿子面」就是將大籽蒿碾碎與麵粉混到一起,做出的麵條筋道又美味。綜合以上幾處紅山文化遺址的浮選結果判斷,紅山文化時期的生業形態應該是農耕生產與採集狩獵並重。紅山文化是一個輝煌的考古學文化,尤其是遼寧凌源牛河梁遺址出土了壯觀的大型壇廟冢群、逼真的泥塑人物和動物造像、精美的玉器和陶器等,令人矚目驚嘆,有學者甚至將紅山文化與中華文明起源相關聯(12)。但是植物考古發現揭示,紅山文化古代先民雖然已經從事農耕生產,卻沒有進入到與其輝煌的文化遺存相匹配的農業社會階段,其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仍然處在由採集狩獵向農耕生產轉變的過渡時期。
興隆溝遺址第三地點是一處夏家店下層文化遺址,從中浮選出土的植物遺存極為豐富,在採集到的百餘份浮選土樣中出土了1.6萬餘粒炭化植物種子,其中以農作物為主,包括粟、黍和大豆三個品種,合計佔所有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99%。事實上,西遼河上遊地區的所有夏家店下層文化考古遺址,只要開展過系統浮選工作,都出土有異常豐富的炭化植物遺存,而且絕大多數都是農作物遺存。例如,赤峰松山區三座店遺址的浮選結果與興隆溝第三地點的幾乎完全一致,在百餘份浮選土樣中出土了10萬餘粒炭化植物種子,其中絕大多數也是農作物遺存,也包括了粟、黍和大豆三個品種(13)。赤峰紅山區二道井子遺址的浮選結果也很相似,在77份浮選土樣中出土炭化植物種子25萬餘粒,也是以栽培農作物為主,包括粟(181600粒)、黍(41200粒)、大豆(179粒)和大麻(3粒)四種農作物,合計數量22萬餘粒,佔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90%(14)。近些年在西遼河上遊地區開展的考古調查項目也同時進行了浮選土品的採集(15),浮選結果顯示,凡是夏家店下層文化土樣都浮選出土了豐富的炭化植物遺存,而且都是以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主,例如在赤峰松山區西道點將臺地點採集的兩份屬於夏家店下層文化土樣,從中浮選出土了炭化粟粒18200粒,炭化黍粒506粒(16)。由此可見,西遼河上遊地區在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正式進入農業社會階段,農耕生產成為當時古代先民物質生活資料的主要來源。
西遼河上遊地區的植物考古揭示,早在距今8000年前的興隆窪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黍和粟兩種栽培作物,當地古代先民在從事採集狩獵活動的同時開始嘗試農耕生產。紅山文化時期,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仍然處在由採集狩獵向農業經濟的轉變過程中,生業形態以農耕與採集並重為特點。在紅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層文化之間,西遼河上遊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出現了一次躍進或質變。雖然以往都是以紅山文化作為西遼河上遊地區考古學文化的核心,但是從植物考古來說,農業社會的建立發生在夏家店下層文化時期。我認為,在西遼河上遊地區的史前考古學文化發展系列中,夏家店下層才是真正的轉折點,標誌著當地的社會發展進入了農業社會階段。
三、黃河下遊地區
黃河下遊地區在考古學研究中也被稱作海岱地區,包括山東省境內以及周邊的皖北、蘇北和豫東。從地理概念上講,這個廣袤地區被稱作黃河下遊有些勉強,因為該地區的南半部實際與黃河無關,屬於淮河水系,例如山東南部的泗、沂、沭流域以及皖北和蘇北,因此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劃分中,大多還是被稱作海岱地區(17)。海岱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序列也比較單純,最早的是後李文化,絕對年代在距今8000年前後,之後順序為北辛文化(距今7000-6100年)、大汶口文化(距今6100-4300年)和龍山文化(距今4300-3800年)。龍山文化之後的嶽石文化已經進入青銅時代。
就全國而言,海岱地區的植物考古工作開展得最充分,收穫也最豐富,這得益於山東大學文化遺產研究院植物考古實驗室的努力。截至目前,在海岱地區開展過浮選工作的考古遺址近50處,根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發表浮選報告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約25處。
開展過浮選工作的後李文化時期的考古遺址有三處:扁扁洞、張馬屯和月莊。扁扁洞遺址位於沂源,是一處洞穴遺址,文化堆積分為三個時期,早期距今10000-9600年,屬於新舊石器時代過渡時期;中期距今9700-9100年,屬於前後李文化;晚期距今7400-6900年,屬於後李文化與北辛文化的過渡期。伴隨發掘開展過小規模浮選工作,出土了7粒炭化黍粒和2粒炭化粟粒,但都出自晚期文化堆積中(18)。張馬屯遺址位於濟南市郊,14C測定年代上限為距今9000年,伴隨發掘採集了118份浮選土樣,出土1286粒炭化植物種子,其中包括6粒炭化黍粒和2粒炭化粟粒(19),這是在海岱地區發現的年代最早的栽培作物遺存。同樣位於濟南的月莊遺址也是一處後李文化遺址,伴隨發掘採集了77份浮選土樣,出土450餘粒炭化植物種子,其中包括黍、粟和水稻三種穀物遺存(20)。月莊遺址浮選結果中最重要的發現是水稻遺存(28粒炭化稻米),證明起源於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水稻早在距今8000年前後已經傳播到了黃河下遊地區,另外還揭示出海岱地區古代農業在後李文化時期就開始顯現出了稻旱混作的跡象或趨勢。
「稻旱混作」不是一個農學概念,是我在考古研究中使用的一個特定概念,專指海岱地區古代農業所表現出的既種植水稻又種植粟黍兩種小米的特殊作物布局(21),我之所以使用這個概念,主要是為了區別其他地區的以種植粟黍為代表的旱作農業和以種植水稻為代表的稻作農業。
雖然水稻早在後李文化時期已經傳播到海岱地區,但稻旱混作農業生產特點遲至大汶口中晚期才逐漸形成。例如,即墨北阡遺址是一處北辛文化晚期至大汶口文化早期的考古遺址,伴隨2009年發掘採集了663份浮選土樣,從中出土炭化植物種子3960粒,其中包括黍粒2914粒,粟粒99粒,但卻沒有發現水稻遺存(22)。而與北阡遺址同處在膠東半島的煙臺午臺遺址是一處大汶口晚期至龍山文化早期的考古遺址,伴隨發掘採集了203份浮選土樣,從中出土炭化植物種子3697粒,其中包括粟粒120粒、黍52粒,稻米25粒(23)。與北阡遺址相比,午臺遺址出土農作物中水稻的比重顯著增加。再如安徽蒙城尉遲寺遺址,在大汶口晚期文化堆積中採集了14份浮選土樣,出土炭化植物種子1560粒,其中包括粟粒386粒、黍23粒,稻米239粒(24),水稻的比重與粟和黍的已經相差無幾。在安徽宿州楊堡遺址的大汶口晚期浮選結果中,水稻的比重甚至超過了粟和黍兩種旱地作物之和(25)。
海岱地區龍山時代考古遺址的植物考古成果非常豐富,其中連續數年開展浮選工作的大型聚落遺址就有聊城教場鋪遺址、鄒平丁公遺址、臨淄桐林遺址、日照兩城鎮遺址、日照堯王城遺址等。據已發表的數據分析,海岱地區龍山時代的古代農業完全承續了大汶口中晚期的稻旱混作傳統。以鄒平丁公遺址2014年度浮選結果為例,在採集到的98份土樣中浮選出土炭化植物種子21523粒,包括粟(10021粒)、黍(1374粒)、水稻(270粒)、大豆(514粒)和小麥(35粒)五種農作物(26)。另外還發現了稻穀基盤和小穗軸6033個(27),可以看出,丁公遺址出土農作物中以粟最多,但水稻也很突出,特別是稻穀基盤/小穗軸的出土數量驚人。其他龍山時代考古遺址的浮選結果大同小異,出土農作物都是以粟、黍、水稻為主。與大汶口中晚期的浮選結果明顯不同的是,龍山時代的浮選結果中水稻的比重有所增加,包括炭化稻粒和稻穀基盤/小穗軸等在內的水稻遺存在出土農作物總數中所佔百分比接近甚至超過粟和黍兩種小米的出土數量。海岱地區龍山時代浮選結果的另外一個變化是,在一些考古遺址如丁公遺址的浮選結果中還出現了大豆和小麥遺存,顯示出當地農業生產開始向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轉化。
黃河下遊地區的植物考古揭示,起源於長江中下遊地區的水稻早在新石器時代早期就已經傳入中國北方的黃河下遊地區,之後一直存在於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產中。在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的浮選結果中,旱田作物黍和粟兩種小米與水田作物水稻同出,說明當地居民既種植旱地作物粟和黍也種植水田作物稻穀,海岱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產特點既不屬於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也不同於中國古代南方稻作農業,而是以種植稻穀和粟類作物並重為特點的一種特殊的稻旱混作農業生產方式。
四、黃河中遊地區
黃河中遊地區在考古學研究中也被稱作中原地區,在新石器時代主要是指仰韶文化的分布範圍,包括河南的大部分區域、陝西的渭河谷地(關中地區)、山西的汾河谷地(晉南)以及河北北部。黃河中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按時間順序分為前仰韶時期(距今8000年前後)、仰韶早期(距今7000-6000年)、仰韶中期(距今6000-5500年)、仰韶晚期(距今5500-5000年)、廟底溝二期(距今5000-4300年)、龍山時代(距今4300-3800年)。由於仰韶文化分布範圍廣、延續時間長、文化內涵豐富,不同區域之間的文化差異較大,因此黃河中遊地區新石器時代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非常複雜,除了仰韶中期即廟底溝文化時期各區域的考古學文化面貌相對一致之外,在其他時期不同區域都有各自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和命名。以渭河谷地為例,前仰韶時期稱作老官臺文化,仰韶早期包括半坡類型和史家類型,仰韶中期即廟底溝文化,仰韶晚期稱作半坡晚期類型,廟底溝二期稱作泉護二期類型,龍山時代稱之為客省莊二期文化。其他區域也是如此,不在此一一贅述。
黃河中遊地區很早就有考古出土植物遺存的報導,例如,20世紀50年代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一件陶罐內發現有炭化粟粒(28);20世紀70年代在河北武安磁山遺址出土的大量小米遺存曾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廣泛關注(29)。磁山小米遺存在出土時已經完全灰化,無法辨識,其種屬的鑑定是根據「灰象法」推斷而成的(30)。最近有學者對磁山遺址小米遺存重新進行了植矽體鑑定,結果發現磁山遺址出土的灰化穀物遺存含有黍和粟兩種小米,以黍為主(31)。
21世紀以來,以浮選法為代表的植物考古在我國考古學界得到迅速發展和普及(32),由於黃河中遊地區是考古學研究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涉及陝晉豫三個考古大省,同時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區域,所以植物考古工作開展得比較系統,取得的成果也較多。據不完全統計,已經發表浮選報告的黃河中遊地區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遺址近30處。
前仰韶時期以分布在河南中部和西部的裴李崗文化最具代表性,其中舞陽賈湖遺址的考古發現最為重要(33)。賈湖也是我國最早開展系統浮選的考古遺址之一,伴隨2001年發掘採集浮選土樣125份,出土了豐富的炭化植物遺存,包括數百粒炭化稻米,以及數量可觀的可食用野生植物遺存,如菱角、蓮藕、橡子、大豆等(34)。量化分析結果揭示,距今8000年前後的賈湖人已經開始從事稻作農業生產,應該還飼養了家豬,但其主要的食物來源仍然依靠採集漁獵。值得指出的是,在賈湖遺址浮選結果中沒有發現粟和黍這兩種北方旱作農業的代表性農作物,這與其他遺址的裴李崗文化時期浮選結果大相逕庭。事實上,關於賈湖遺址的文化屬性仍存爭論,發掘者張居中先生認為賈湖遺存具有獨特的文化面貌,有別於裴李崗文化,應該命名為賈湖文化(35);但其他學者認為賈湖遺存與裴李崗文化遺存大同小異,可以稱之為裴李崗文化賈湖類型(36)。賈湖遺址浮選結果的分析似乎更支持張居中先生的觀點。
仰韶文化時期的植物考古以魚化寨遺址浮選結果最為全面。魚化寨遺址位於西安市內,是一處仰韶文化時期的村落遺址,文化堆積以仰韶早期(半坡類型和史家類型)和仰韶晚期(半坡晚期類型)為主,仰韶中期(廟底溝文化)遺存較少。伴隨發掘採集浮選土樣103份,從中出土了種類豐富、數量驚人的炭化植物遺存,僅植物種子就多達29萬餘粒,但其中絕大多數(23.5萬粒)是從一個仰韶早期灰坑中出土的藜屬(Chenopodium)植物種子。其餘的5.6萬粒植物種子分別屬於20餘個種屬,包括粟(3.6萬粒)、黍(1.4萬粒)、水稻(5粒)三種穀物遺存(37)。魚化寨遺址浮選結果顯示,仰韶文化時期的農耕生產是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特點,屬於典型的古代北方旱作農業傳統。魚化寨遺址植物考古研究的最大收穫是揭示了仰韶文化的農業經濟發展過程。在仰韶早期,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特點的旱作農業並沒有完全取代採集狩獵成為經濟主體,通過採集獲得的野生植物如藜屬種子、菱角等仍是當時的重要食物資源之一。隨著技術和社會發展,仰韶文化經濟生活中的農耕生產比重逐漸增強,採集活動作用逐漸降低。當發展到仰韶中期即廟底溝時期,通過採集野生植物獲取食物資源的必要性已經微不足道,旱作農業終於取代採集狩獵成為仰韶文化的經濟主體,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北方地區正式進入以農業生產為主導經濟的社會發展階段,即農業社會階段(38)。
黃河中遊地區開展過浮選工作的龍山時代考古遺址數量很多,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河南的禹州瓦店遺址、登封王城崗遺址(39)、洛陽王圪壋遺址、淮陽平糧臺遺址、鶴壁大賚店遺址(40),山西的襄汾陶寺遺址(41)、運城周家莊遺址(42),陝西的扶風周原遺址(43)、扶風案板遺址等。這些遺址的浮選結果呈現了一個共同的現象,即出土的植物遺存中都包含有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麥五種不同的農作物遺存。以禹州瓦店遺址為例(44),在採集的255份土樣中,浮選出土炭化植物種子12190粒,其中包括粟(5253粒)、黍(1110粒)、水稻(稻米1231粒,基盤135粒)、大豆(905粒)和小麥(22粒)五種農作物,合計佔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71%。再以洛陽王圪壋遺址為例(45),伴隨發掘採集了25份土樣,浮選出土炭化植物種子4491粒,其中包括粟(2626粒)、黍(168粒)、水稻(144粒)、大豆(580粒)和小麥(1粒)五種農作物,合計佔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78%。還有淮陽平糧臺遺址(46),伴隨發掘採集了59份土樣,浮選出土炭化植物種子4384粒,其中也是包括了粟(2876粒)、黍(310粒)、水稻(2粒)、大豆(80粒)和小麥(2粒)五種農作物,合計佔出土植物種子總數的75%。通過量化分析發現,在這些龍山時代考古遺址浮選出土的五種農作物中,粟在出土數量和出土概率的統計數值上都明顯地高於其他四種農作物品種,黍的絕對數量雖不突出,但出土概率一般不低,這表明粟和黍這兩種小米始終是黃河中遊地區新石器時代農業生產的主體農作物。
植物考古發現揭示,黃河中遊地區的古代農業屬於典型的古代北方旱作農業傳統,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特點。然而自仰韶晚期起,黃河中遊地區的農業生產狀況處在不斷變化的動態過程中,水稻、大豆和小麥這三種輔助性農作物伴隨著時代的進程逐漸出現或比重不斷增加。發展到龍山時代,黃河中遊地區的農業生產五種農作物品種齊全,農作物布局逐漸趨向複雜化,由相對單一的粟作農業向包括水稻、小麥和大豆在內的多品種農作物種植制度轉化。
五、黃河上遊地區
黃河上遊地區在考古學研究中也被稱作西北地區,但與我國行政區劃的西北地區概念完全不同,僅局限在流經甘青地區的黃河上遊段及其支流,如青海東部的湟水和大通河流域,甘肅中南部的莊浪河、洮河和大夏河流域、隴東的渭河上遊,另外還有河西走廊。黃河上遊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可以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前段主要集中在渭河上遊地區,文化面貌與黃河中遊渭河谷地的仰韶文化基本相同,包括大地灣一期文化(距今8000年前後)、仰韶早期(距今7000-6000年)和仰韶中期(距今6000-5500年);後段自仰韶中晚期起,逐步發展和演變成為具有當地特色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即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其中馬家窯文化又分為三個類型,馬家窯類型(距今5300-4600年)、半山類型(距今4600-4300年)和馬廠類型(距今4300-4000年)。齊家文化的絕對年代有爭議,目前一般認為應該在距今4200-3600年間。
黃河上遊地區的植物考古工作發展較快,特別是近些年來伴隨考古發掘在許多遺址都開展了浮選工作,但目前發表的資料不多。
黃河上遊地區前段即仰韶文化時期的植物考古以大地灣遺址的發現比較重要。大地灣遺址位於天水秦安縣,文化堆積分為四期,包含了仰韶文化各時期(47)。在大地灣一期文化堆積中出土了少量的炭化黍粒,這是黃河上遊地區發現的最早的農作物遺存;大地灣二期即仰韶早期出土了黍和粟兩種小米遺存,其中以炭化黍粒的出土數量最多;大地灣三期即仰韶中期未見植物遺存,原因不詳;大地灣四期即仰韶晚期也出土了粟和黍兩種小米遺存,但以粟粒的出土數量為多(48)。大地灣遺址出土植物遺存不僅為探討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和傳播提供了重要的信息,而且還揭示了旱作農業的主體農作物由黍向粟轉變的發展規律。
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時期的植物考古主要集中在洮河流域和青海東部地區,近些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植物考古實驗室和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植物考古實驗室聯合在該地區的幾處重要考古遺址開展了浮選工作,包括甘肅的臨洮馬家窯遺址(馬家窯文化和齊家文化)、岷縣山那樹扎遺址(馬家窯文化)、臨潭陳旗磨溝遺址(仰韶晚期和齊家文化),青海的民和喇家遺址(齊家文化)等,另外,蘭州大學西部環境和氣候研究院在青海互助金蟬口遺址(齊家文化)和甘肅臨夏李家坪遺址(齊家文化)開展的浮選工作也很重要。這些遺址的浮選結果都未正式發表,暫不能公布詳細數據,但綜合各遺址的分析結果可以看出,馬家窯文化的生業是以農業為主,農耕生產屬於以種植粟和黍兩種小米為主的古代北方旱作農業傳統。齊家文化早期延續著馬家窯文化時期的農業特點。但到了齊家文化中晚期,當地生業經濟發生了顯著變化,首先是小麥和大麥的出現,麥類作物逐步替代粟和黍兩種小米成為黃河上遊地區農業生產中的主體農作物;其次是家畜飼養的比重增加,社會經濟逐漸向農耕生產與家畜飼養並重的生產經營方式轉變。
從地理概念上講,河西走廊不屬於黃河上遊地區,因為河西走廊內的三大水系均為祁連山融雪形成的內陸河,與黃河無關。但是在考古學文化區系類型劃分上,西北地區包括了河西走廊,因為馬家窯文化特別是馬廠類型和齊家文化的分布範圍都擴展到了河西走廊。早在20世紀80年代,位於張掖民樂縣的東灰山遺址發現了炭化小麥,農學家李璠先生對出土小麥進行了鑑定和分析,並根據採自遺址黑炭土的14C測年結果,推斷東灰山小麥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後(49)。如是,東灰山小麥則是在中國境內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小麥遺存,曾引起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和爭論(50)。近年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組成聯合考古隊,重返東灰山遺址開展植物考古工作,採集浮選土樣22份,出土炭化植物種子7474粒,其中包括粟(4198粒)、黍(331粒)、小麥(98粒)和大麥(1170粒)五種農作物,另外還發現了1146個大麥的小穗軸(51)。北京大學碳十四實驗室應用加速器質譜測年方法對十餘粒出土麥粒直接進行年代測定,測年結果均落在了距今3600~3400年之間(52)。另外,環境學者也在近期對東灰山遺址出土小麥進行了採樣和AMS年代測定,校正年代為3829~3488cal.BP(53)。這些測年數據證實東灰山遺址的文化堆積及其包含的麥類作物遺存應該屬於四壩文化,絕對年代在距今3600年前後。由此,困擾學術界數十年的一樁疑案終於得到解決。
在河西走廊,西城驛遺址的浮選結果也很重要。西城驛遺址位於張掖市郊,文化堆積分為三個時期,馬廠類型晚期(距今4100-3900年)、西城驛文化(距今3900-3700年)和四壩文化早期(距今3700-3500年)。伴隨2012年和2014年考古發掘,採集浮選土樣179份,出土炭化植物種子29612粒,包括粟(16364粒)、黍(5205粒)、小麥(1373粒)、大麥(433粒)、大麻(2粒)五種農作物(54)。其中的小麥、大麥和大麻全部都出土自屬於四壩文化的浮選樣品,而馬廠類型晚期和西城驛文化的浮選樣品僅出土粟和黍兩種小米。伴隨西城驛遺址2010年的發掘也採集了少量浮選土樣,其中17份屬於西城驛文化時期,2份屬於四壩文化時期,浮選結果與2012/2014年度的大同小異(55)。根據西城驛遺址浮選結果分析,河西走廊與黃河上遊地區基本相同:以馬廠類型和西城驛文化早期為代表的新石器時代古代農業屬於典型的以種植粟和黍為主的北方旱作農業,但發展到青銅時代(即西城驛文化晚期和四壩文化),麥類作物取代粟和黍兩種小米成為河西走廊地區古代農業生產的主體農作物,這種由種植小米向種植麥類作物的轉變過程發生在西城驛文化時期。
①趙志軍:《植物考古學的學科定位與研究內容》,《考古》2001年第7期。
②趙志軍:《植物考古概述》,《南方文物》2019年第3期。
③趙志軍:《植物考古學的田野工作方法——浮選法》,《考古》2004年第3期。
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考古研究所:《陝西宜川縣龍王辿舊石器時代遺址》,《考古》2007年第7期。
⑤翟少東:《半畝方塘,源頭活水——記2017年國際磨製石器協會第二次會議》,《中國文物報》2017年11月17日。
⑥[日]森川敬子、堀田希一:《炭素測定法を補正一青森ほ1萬6500年前の土器片》,《文化財發掘出土情報》,(6)8-10。
⑦傅憲國:《嶺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考古學研究(九)》,科學出版社,2012年;趙朝紅、吳小紅:《中國早期陶器的發現、年代測定及早期制陶工藝的初步探討》,《陶瓷學報》2000年第4期。
⑧Wu Xiaohong,Chi Zhang,Paul Goldberg,et al.「Early Pottery at 20,000 Years Ago in Xianrendong Cave,China」.Science Vol.336,1696-1700,2012.
⑨趙志軍:《從興隆溝遺址浮選結果談中國北方旱作農業起源問題》,南京師範大學文博系編《東亞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
⑩孫永剛、趙志軍:《魏家窩鋪紅山文化遺址出土植物遺存綜合研究》,《農業考古》2013年第3期。
(11)孫永剛、趙志軍、吉平:《哈民忙哈史前聚落遺址出土植物遺存研究》,《華夏考古》2016年第6期。
(12)劉國祥:《探尋紅山文化與中華五千年文明源頭》,《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10月31日第8版。
(13)趙志軍:《中華文明形成時期的農業經濟發展特點》,《國家博物館館刊》2011年第1期。
(14)孫永剛、趙志軍、曹建恩等:《內蒙古二道井子遺址2009年度浮選結果分析報告》,《農業考古》2014年第6期。
(15)Zhao Zhijun.「Plant remains」.In Chife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v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ed):Settlement Patterns in the Chifeng Region.Center for Comparative Archaeology,University of Pittsburgh.pp 27-34.2012。
(16)賈鑫、孫永剛、楊金剛等:《西遼河上遊地區夏家店文化時期浮選結果與分析》,《農業考古》2017年第6期。
(17)欒豐實:《海岱龍山文化的分期和類型》,載《海岱地區考古研究》,山東大學出版社,1997年。
(18)Sun Bo,MaykeWagner,Zhao Zhijun et al.Archaeological discovery and research at Bianbiandong early Neolithic cave site,Shandong,China.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Volume 348,2014,169-182。
(19)吳文婉、靳桂雲、王興華:《海岱地區後李文化的植物利用和栽培:來自濟南張馬屯遺址的證據》,《中國農史》2015年第2期。
(20)Gary Crawford、陳雪香、欒豐實等:《濟南長清月莊遺址植物遺存的初步分析》,《江漢考古》2013年第2期。
(21)趙志軍:《兩城鎮與教場鋪龍山時代農業生產特點的對比分析》,載《東方考古》(第1集),科學出版社,2004年。
(22)王海玉、靳桂云:《山東即墨北阡遺址(2009)炭化種子果實遺存研究》,載《東方考古》(第10集),科學出版社,2013年。
(23)陳松濤、孫兆鋒、吳文婉等:《山東午臺遺址龍山文化聚落生計的植物大遺存證據》,《江漢考古》2019年第1期。
(24)趙志軍:《浮選結果分析報告》,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蒙城縣文化局編著《蒙城尉遲寺》(第二部),科學出版社,2007年。
(25)程至節、楊玉璋、袁增箭等:《安徽宿州樣堡遺址炭化植物遺存研究》,《江漢考古》2016年第1期。
(26)吳文婉、姜仕煒、許晶晶、靳桂云:《鄒平丁公遺址(2014)龍山文化植物大遺存的初步分析》,《中國農史》2018年第3期。
(27)水稻在生長過程中每一粒稻穀都是通過小穗(spikelet)與稻穗相連,連接部位在小穗上稱作「小穗軸」,在穀粒上稱作「基盤」。栽培稻和野生稻在生物特性上最根本的區別之一是栽培稻喪失了成熟後自然落粒的功能,這與小穗軸和基盤相互連接面的形態特徵直接相關,因此基盤和小穗軸的形態特徵就成為考古界用以判別栽培稻和野生稻的重要標誌。
(28)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陝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館編著:《西安半坡——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遺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第5-8頁。
(29)佟偉華:《磁山遺址的原始農業遺存及其相關的問題》,《農業考古》1984年第1期。
(30)黃其煦:《灰象法在考古學中的應用》,《考古》1982年第4期。
(31)Lu Houyuan,Zhang Jianping,Liu Kam-biu et al.Earliest domestication of common millet(Panicum miliaceum)in East Asia extended to 10,000 years ago.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2009,106(18):7367-7372.
(32)趙志軍:《植物考古學及其新進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舞陽賈湖》,科學出版社,1999年。
(34)趙志軍、張居中:《賈湖遺址2001年度浮選結果報告》,《考古》2009年第8期。
(35)張居中:《略論淮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36)韓建業:《裴李崗文化的遷徙影響與早期中國文化圈的雛形》,《中原文物》2009年第2期。
(37)趙志軍:《仰韶文化時期農耕生產的發展和農業社會的建立——魚化寨遺址浮選結果的分析》,《江漢考古》2017年第6期。
(38)趙志軍:《中國農業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發現》,《光明日報》理論版,2019年8月5日第14版。
(39)趙志軍、方燕明:《登封王城崗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華夏考古》2007年第2期。
(40)武欣、郭明建、王睿等:《河南鶴壁大賚店遺址龍山時期植物遺存分析》,載《東方考古》(第14集),2018年。
(41)趙志軍、何努:《陶寺城址2002年度浮選結果及分析》,《考古》2006年第5期。
(42)蔣宇超、戴向明、王力之等:《大植物遺存反映的龍山時代山西高原的農業活動與區域差異》,《第四紀研究》2019年第1期。
(43)趙志軍、徐良高:《周原遺址(王家嘴地點)嘗試性浮選的結果及初步分析》,《文物》2004年第10期。
(44)劉昶、趙志軍、方燕明:《河南禹州瓦店遺址2007、2009年度植物遺存浮選結果分析》,《華夏考古》2018年第1期。
(45)鍾華、吳葉恆、張鴻亮等:《河南洛陽王圪壋遺址浮選結果及分析》,《農業考古》2019年第1期。
(46)趙珍珍、曹燕鵬、靳桂云:《淮陽平糧臺遺址(2014-2015)龍山時期炭化植物遺存研究》,《中國農史》2019年第4期。
(47)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秦安縣大地灣遺址仰韶文化早期聚落髮掘簡報》,《考古》2003年第6期。
(48)劉長江、孔昭宸、朗樹德:《大地灣遺址農業植物遺存與人類生存的環境探討》,《中原文物》2004年第4期。
(49)李璠、李敬儀、盧曄等:《甘肅省民樂縣東灰山新石器遺址古農業遺存新發現》,《農業考古》1989年第1期。
(50)李水城、莫多聞:《東灰山遺址炭化小麥年代考》,《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6期。
(51)蔣宇超、王輝、李水成:《甘肅民樂東灰山遺址的浮選結果》,《考古與文物》2017年第1期。
(52)Flad,R.,Li Shuicheng,Wu Xiaohong,et al.「Early wheat in China:results from new studies at Donghuishan in the Hexi Corridor」.The Holocene 20(6),2010.pp 955-965.
(53)Dodson,J.,Li Xiaoqiang,Zhou,X.,et al.「Origins and spread of wheat in China」.Quaternary Science Reviews 72,2013.pp 108-111.
(54)範憲軍、陳國科、靳桂云:《西城驛遺址浮選植物遺存分析》,載《東方考古》(第14集),2018年。
(55)蔣宇超、陳國科、李水成:《甘肅張掖西城驛遺址2010年浮選結果分析》,《華夏考古》2017年第1期。
來源:《中國農史》
,





![2022愛方向和生日是在[質量個性]中](http://img.xinsiji.cc/20220215/1604989894118215680.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