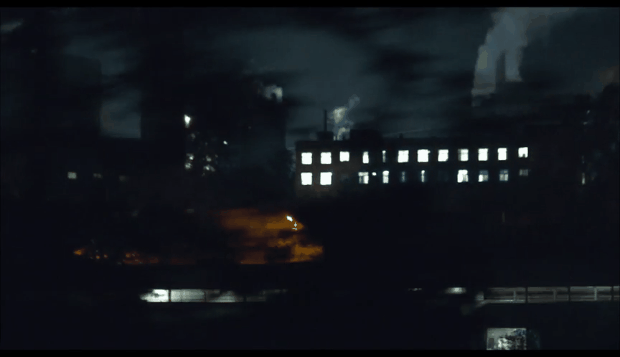暴力兔子電影在線(不是所有電影都能套殼女性主義)
2023-08-05 03:29:52 1
《長津湖》《罐頭小人》《五個撲水的少年》,受疫情影響,原本指望著撐場的電影輪番撤檔。
值得大家走進電影院的新片,只剩下這部《兔子暴力》。
然而當我走出電影院,卻只想說,這天,可真涼啊。

01.
《兔子暴力》的靈感來源,是一起舊案。
兩個女學生被綁架,報案後其中一位平安歸來,聲稱另一女生是去外地見網友。
真相是,她為了幫母親還貸,二人合謀綁架並謀害了自己的同學。
說兩處值得一提的細節,一是為了不讓女兒成為主謀,母親選擇親自動手。
二是女兒扛住了8小時的審訊,意圖包庇母親。
未成年犯罪,還有張力十足的人物關係、扭曲的愛,人性的灰色地帶。
拋開道德與法律意識,這確實是拍犯罪片的好素材。

在此基礎之上,本片塑造了一對有別於以往國產電影的母女形象。
先看萬茜飾演的曲婷。
正如埃萊娜·費蘭特在《碎片》中的總結,「沒有任何人,包括母親的裁縫會想到母親有一具女性的身體。」
過去的國產電影往往會忽略母親所具備的另一重屬性:女人,習慣將母親視作「去性化」的符號。
難能可貴的是,本片打破了這種常規。
登場時,曲婷身著一襲黃裙,蓬鬆捲髮,輕叼著煙,一派慵懶、性感的模樣。
只消幾個眼神,便把水青逗弄得掉頭就跑。
她從未見過舉止如此輕佻的女人。
與之相比,水青的繼母才是最常見的小鎮婦女,質樸、市儈,一頭扎進家庭,疏於打扮。

曲婷第一次帶水青回到舊劇場,繪聲繪色地講述她當年登臺時打扮成吉普賽女郎驚豔全場的往事。
在水青的想像裡,那時的曲婷簡直美到不可方物。

除了剝開父權社會籠罩在女性形象之外的那層束縛,本片還釋放了母親被壓抑的「情慾」。
有意無意,鏡頭時常會展現曲婷介於「少女」與「熟婦」之間的魅力。
比如,曲婷帶同學們練舞的場景。
明明是一本正經的教學,但她偏偏不知收斂,還是那幅若有若無的撩人姿態,臉貼臉地搭著男生的肩膀。
在其他人看來,這無異於一種勾引。

黃裙、黃車、黃色外套、芒果,包括戒指,反覆出現的「黃色」意象,無疑是在強調曲婷所擁有的生命力與吸引力。
而對這個小鎮來說,曲婷的魅力越大,就越是格格不入,越是危險。
這裡的「危險」指的不是她像《致命女人》中親手弒夫的貝絲,而是指她拒絕被男性和傳統道德馴服。
女兒剛滿一歲時,曲婷便離開了,她甘願流浪異鄉,也不願和平庸的男人共度一生。
從那之後,她也時常招蜂引蝶。
被她一撩即中的白皓文、覬覦她許久的老杜、警察局裡一眼就認出她的老同學,就連前夫也留著戒指,似乎還在幻想她有朝一日會回家。
你可以說這是輕浮、浪蕩,也可以理解為一種自由。

再看李庚希飾演的水青。
從小被拋棄的她極度渴望被愛,默默收集了所有與母親有關的東西。
二人重逢後,她再三強調不會打擾對方的生活,只想討個小物件,留個念想。
後來兩人相處時,她也態度卑微,不敢奢求太多,只敢小心翼翼地保持距離。
這麼看,她似乎只是個心思敏感的青春期少女。

但正如片名所揭示,隱藏在「兔子」柔弱皮囊之下的,是殘暴。
她就像《隱秘的角落》裡的朱朝陽,時而天真,時而冷血。
一旦時機成熟,「惡童」本質便暴露無遺——
哪怕犯罪,她也要守住這份失而復得的母愛。

不同於《你好,李煥英》裡溫馨、動人的母女情,《兔子暴力》裡的母女情瀰漫著病態、陰翳的氣息。
相比起舉止幼稚,總是任性而為的曲婷,水青時常會扮演「母親」角色。
除了給她包紮傷口,勸她少喝酒,當母親感到尷尬時,還會主動勸慰她,「不必刻意演母女」。
這段錯位的母女關係,正是全片最重要的劇情線。
但很遺憾,創作者似乎沒想明白該怎樣準確表達水青對曲婷的眷戀和依賴,乾脆讓她表現得像個情竇初開的少女。
於是,才有了這段「隧道表白戲」。

想像下,如果把曲婷換成男生,水青的種種舉動也完全成立。
因為暗戀,所以要瘋狂偷看,因為憐惜,所以要趁對方睡著,偷偷親吻額頭。
so,真的不能怪別人想歪,誤以為《兔子暴力》在打「母女百合」擦邊球。
主要是片中的表現手法實在太像純愛片,母女倆的相處氛圍也過於曖昧,有點橘裡橘氣。

好在,最後這場戲拉了點好感度。
渡口邊,水青如約實施了綁架計劃,準備向馬悅悅父親勒索200萬。
事到臨頭,曲婷卻慫了,她沒想到女兒居然來真的。
再一想到水青被拋棄多年卻願意為她犧牲一切,曲婷只好哭著勸女兒趕緊收手。

這時,突然來了一群蹦野迪的路人。
為了不被發現,兩人死死按住馬悅悅,直到對方咽氣。
意識到事態不妙,水青忍不住崩潰大哭。
剛才還不知所措的曲婷一把抱住水青,用顫抖卻堅定的語調安慰她,「讓媽媽來搞。」
生死關頭,這隻晚熟的「雌鳥」終於張開羽翼,保護她的雛鳥。
而「雛鳥」也得償所願,投入母愛的懷抱。
這無疑是全片最感人的一幕。

影片上映後,有觀眾給出差評,理由是影片美化犯罪,洗白殺人犯。
有一說一,對比原型,《兔子暴力》實際已經加了層濾網,篩掉了那些粗糙、扎人的顆粒:
原本的謀殺改成殺人未遂、母女倆的合謀改成了由女兒主導、警方破案改成曲婷中途自首。


在申瑜的理解中,母女倆就像《巴黎聖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和愛絲梅拉達,彼此守護,彼此救贖。
誠然,導演擁有最終解釋權,如何改編是她的自由。
作為觀眾,我單純覺得有點可惜,故事明明可以往更暗黑、大尺度的方向走,比如描繪水青內心的瘋狂與執念,或者挖掘曲婷不堪的過去,從而深層次地構建出畸形的母女關係。
你想,被拋棄了十多年,水青心中難道沒有一絲怨言?
她之所以犯罪,除了想救母,心底是否還有種自毀的衝動?
曲婷說過,她從小到大沒有養過女兒,感情不深。
那面對女兒的主動,她難道沒想過順勢甩鍋,逃之夭夭?
各懷私心,各有各的陰暗面,最終卻被「愛」捆綁,齊齊走向毀滅。
這不挺帶感?

「希望用悲劇故事傳遞出一種溫暖的東西。」
如導演所說,她確實令故事畫風變得很溫情。
同時,這種無害化處理也削弱了人物張力,導致故事帶來的震撼大打折扣。
再配上結尾的字幕,不僅直接把「正能量」打在公屏,甚至替觀眾概括好了中心思想:
「本片的宗旨,在於警示社會和家庭應當給予青少年更多的關愛」。
除了鼓掌,還能說什麼?
02.
相比起傳統犯罪片,《兔子暴力》具備一定作者性,有著文藝腔滿滿的臺詞、意識流鏡頭。
比如水青在江邊入睡時的詭異夢境、兔子幫在隧道裡合唱《樂園》的橋段、金熙在廣播站裡念的詩。

還有大結局,柔光濾鏡一打,水青衝著鏡頭一笑,不知道的還以為電影改編自哪本青春疼痛文學。

文藝片與犯罪片風格的拼貼與糅雜,最終導致了各種排異反應。
最明顯的,是整個故事變的支離破碎,過於情緒化。
比如,在父母的爭吵聲中,金熙邊哭邊自殘。
顯然,這是想揭示角色叛逆背後的不幸。
嗯,道理誰都懂,但還是不禁想問上一句,然後呢?
明明前期有的是時間來展開,為啥非要臨到收尾才匆匆補這麼一筆?

像這類意義不明的支線,片中還真不少。
尤其是馬悅悅那個有暴力傾向的親爹,又是剁魚,又是自扇耳光,貌似很有戲。
看似沉默憨厚的老父親,內心不僅深藏著被生活壓榨的苦悶,又有面對「階級鴻溝」的自卑,壓抑多年的負面情緒隨時可能失控。
就在我瘋狂腦補這座「活火山」將如何爆發時,他的戲份戛然而止…
辛辛苦苦鋪墊半天,就這?
真的,我誠懇地建議各位編劇最好把「契訶夫法則」刻煙入肺,別讓第一幕埋下的雷,直到大結局還是發啞炮。

對了,說到這,怎麼能不提真·文藝片勞模黃覺?
我已經數不清這是他第幾次友情客串——
《那一場呼嘯而過的青春》,黃覺演愛上技校女神的黑幫老大:《灰燼重生》裡,黃覺給男主戴了綠帽;《被光抓走的人》裡他的任務就是勾搭男主老婆。
還有《南方車站的聚會》,他演的是強暴女主的路人。
這回,他又跑來演對女主有好感的催債大哥。
我說,黃覺是內地銀幕行走的「性符號」第一人,應該沒人反對吧?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麼?
是老杜這個角色本意是為了體現父權社會對於底層女性的迫害,強調「美貌」之於女性有時宛若「原罪」。
偏偏,他的大尺度戲份在上映時又被刪減了,真就來打個醬油唄。

各種碎片化敘事、可有可無的支線、功能性角色,足以折射出導演對於敘事節奏把控的無能。
更關鍵的是,本片為了點「女性情誼」的題,中途還插入了所謂「兔子幫」的情節。
然而,正是這個小團體讓故事變得更割裂。
說真的,直到走出電影院,我都沒搞懂金熙的人物邏輯。
別的不說,就說她到底和其他角色熟不熟?
她一會兒和馬悅悅鬧翻,一會兒又和她勾肩搭背,陪她去買飲料。
明明馬悅悅是好心幫腔,讓她別欺負水青,她又開始陰陽怪氣,一副「老子誰也看不爽」的態度。
一開始,她瞧不起曲婷,給水青吹耳邊風,勸她千萬別理她媽。

再一眨眼,四人居然湊成一桌,舉杯歡慶,大有不醉不歸的架勢。

還沒完呢,她們後來又大半夜的不睡覺,組團跑隧道裡合唱《樂園》,儼然一副親親熱熱好姐妹的樣子。
我就整不明白了,這四人是怎麼回事。
除了排舞,明明彼此間也沒啥別的互動,這就同性相吸了?
是,曲婷的性格和心態都挺年輕,和真·花季少女們待在一塊也沒啥違和感,那好歹多交待幾句吧。
更迷惑的,是經歷了隧道合唱之後,「兔子幫」就原地解散了。
害,敢情還是個限定女團,出道即巔峰。
罷了,單飛就單飛。
問題是,2021年了,咋還有人把「變臉」和「撕逼」當成姐妹花的傳統藝能。
金熙嫉妒曲婷撩了白皓文,轉頭和水青大吵一架,就差沒說「你媽是個賤貨」。

後來,水青當眾念了一封信,既是她的自述,也算是求和。
一通操作下來,兩人看似和好了,可等水青求金熙陪她過生日,她又逃得比兔子還快。
小團隊說散就散,姐妹說掰就掰,人物情緒轉變之快,讓人恍恍惚惚紅紅火火,仿佛夢回《小時代》。

看得出來,導演屬實無法駕馭自己的表達欲。
該深挖的不深挖,該解釋的又不解釋。
經典的能一波打團,非要強行多線程,攪得整部片子就像一坨亂麻。
03.
該聊的都差不多了,最後再多聊幾句本片的「畫外音」——
申瑜導演對於城市與個體的人文關懷。
在這裡,先摘一段三聯生活周刊的報導——
「本刊記者發現,無論是馮家、李家還是尹藝的父母都是南京老工廠的下崗工人,對孩子的教育重視但不得要領。」
「我們20年工齡只拿到7800塊錢,靠這點錢創業,每天辛苦幹活才能維持一家人的溫飽。」尹藝的父親承認對女兒教育力不從心。
魏濤發現,南湖的初中裡單親家庭的比率相當高,「初三分班時,李園原來的班分過來5個學生,其中兩個是單親家庭。如果當年給李園更多一些關心,是不是就不會出這樣的事?」
————《南京母女綁架殺人案:母愛的代價》
下崗,城市發展進程中的一處小小偏差,改變了無數家庭的命運。
個體的悲劇,也脫離不開時代的勾連。
受此啟發,導演在影片開場加了一段城市側寫:
吞吐廢氣的巨型煙囪、曲婷記憶中的破敗廠房、鏽跡斑斑的橋梁、白沫滾滾的金沙渡口。
對於攀枝花這座工業城市而言,工廠不僅是推動經濟的燃料,也是昔日輝煌的見證。
等到工業衰退,工廠舊址便成了彌留的殘影,城市居民的共同記憶。
再往下看,你會發現三個女孩有著相似的家庭背景:
都是單親家庭,由父親帶大,水青和馬悅悅的父親曾是老工廠工人,下崗後才另謀生路。
不僅如此,她們還面臨著相似的困境。
被後媽排擠的「局外人」水青始終期盼母親的歸來;馬悅悅想逃離父親的掌控,嚮往自由生活;金熙厭倦了父母不休的爭吵,渴望親情的關懷。
某種程度上,她們都是從社會的齒輪裡脫離,在縫隙裡浮浮沉沉的邊緣人。
從這個角度來看,《兔子暴力》就如同「東北文藝復興」的變體,是一次對於時代落水者的探視與體察。
只可惜,就像劇情裡「兔子幫」短暫地將她們縫合在一起,爾後又各自散落。
導演的表達功力決定了影片只能用委婉的方式敲敲邊鼓,再用臺詞來戳穿小鎮衰敗的真實面貌:
「這是個青春痘一樣的城市」、「看上去萬物光明,其實布滿了潰瘡。」
一般人可能get不到導演的用意,更別提深入去思考個體的命運究竟是如何受到時代的牽制。
說白了,就是執行力跟不上想法,支楞不起來。
我們的生活本是座富礦,而電影又是連接「個體」與「時代」的橋梁。
《兔子暴力》的失利,除了值得惋惜,也讓我忍不住去想,我們是否還能擁有個人與時代發生強關聯,稱得上「硬現實主義」的電影。
如果不能,那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後,時移世易,我們該到哪裡去找尋那些被遺忘的人,找尋時代的蹤跡?
同樣是青少年犯罪題材,我們何時才能等到下一部《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END-
互動話題
你最近看的院線片是哪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