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開夜合的小說北城有雪(小說推薦露水的夜作者)
2023-06-08 04:02:23
明開夜合的小說北城有雪?南笳和周濂月認識,是因為解文山老師,否則她多半一輩子接觸不到這樣金字塔頂端的人,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關於明開夜合的小說北城有雪?以下內容大家不妨參考一二希望能幫到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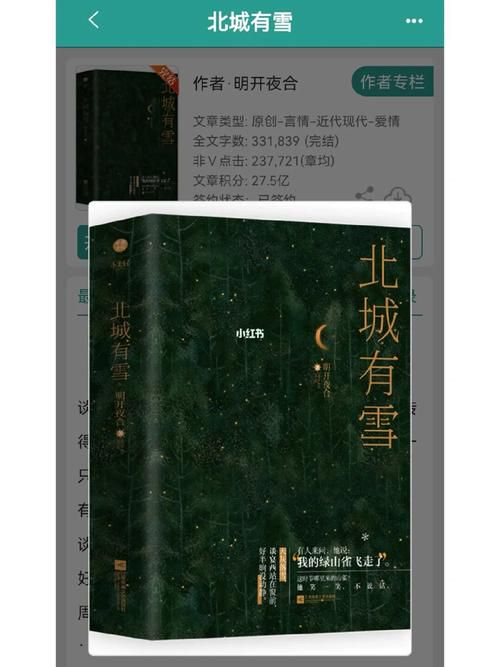
明開夜合的小說北城有雪
南笳和周濂月認識,是因為解文山老師,否則她多半一輩子接觸不到這樣金字塔頂端的人。
那真是亂糟糟的一天——
話劇團今年新排了一齣劇目,沉浸式的先鋒題材,首演超出預期地成功。
劇團定了第二天慶功,從傍晚一直喝到深夜。
南笳在包房裡睡了一覺,醒來已經快到晚上十一點。
包房裡太吵,南笳這一陣又缺覺少眠,實在扛不住了,準備先走。
好友陳田田喝得半醉,頭疼欲裂,因為南笳住得不遠,就想去她家借住一晚。
南笳叫了部車,載上陳田田一塊兒走了。
計程車停在胡同口,南笳習慣性地往沿街的鋪面那兒看了一眼——解文山解老師開了一家專售舊書古籍的書店,就在這條街上。
已經要到十一點半了,書店一樓燈還亮著。
南笳覺得有點奇怪,一時駐足。
解文山的書店商業和居住兩用,一樓賣書,二樓居家。他上了年紀,覺變少了,又嗜好看書,一般晚上書店關門以後,還要看書寫字一兩個小時才會上床。
但無論如何,通常不會晚過十一點,就一定會關了一樓門上樓去。
南笳扶了扶半掛在自己身上的陳田田,「還站得穩嗎?你等我一會兒,我去跟解老師打聲招呼。」
陳田田也是認識解文山的,曾經跟南笳一起去他那兒蹭過飯,便說:「我也去。」
書店門沒關,南笳徑直推門進去。
店裡亮著燈,香插裡檀香未滅,前堂卻沒人。
南笳更覺奇怪,這不是解老師的風格,他只要出門,總會記得熄滅一切明火,怕引起火災。
南笳喚了兩聲,沒聽見聲響,見通往後間的移門開了一線,說一聲「打擾了」,將門推開。
解文山雙目緊閉,癱倒在水泥地上,像是一攤沒了形狀的橡皮泥。
南笳腳都嚇軟了,幾步跑過去,「噗通」一聲跪在地上,輕搡解文山肩膀,毫無反應。她哆嗦著伸手摸頸側大動脈,還有脈搏。
立即吩咐陳田田:「田田,打120!」
陳田田也給嚇清醒了,趕緊掏手機打急救電話。
南笳經歷了有生以來最漫長的五分鐘,直到外頭傳來「嗶嗚嗶嗚」的急促聲響。
南笳和陳田田跟著救護車去了醫院,解文山直接被推進急救室。
南笳等在走廊裡,背靠著牆壁,一背的冷汗,全身發涼。
陳田田捉她的手,輕輕捏了下,「還好吧?」
南笳無聲點頭。
「放心,解老師一定能化險為夷。」
「嗯。」
陳田田又問:「想來根煙嗎?」
「這裡不讓。」
「外面抽去?」
南笳笑了笑,「沒事,不用的。你陪著我我已經好多了。」
南笳強迫自己到長椅上坐下,耐心地等。
度秒如年,不知道過去多久,總算等到「急救中」的燈滅了。
一個護士推門出來通知她,解文山已經脫離危險,一會兒就轉到病房去。
約莫十來分鐘,解文山被推了出來。
他鼻孔裡插著氧氣鼻管,看著只像是睡得很沉,南笳有點不敢確定,手碰了碰他的手臂,皮膚是冰涼的,但她大拇指觸到了他手腕的脈搏,總算放心。
南笳去辦了住院手續,回到病房,守了半個多鐘頭,解文山甦醒了。
護士過來做了些檢查,體徵一切正常,南笳放下心來,準備回去給解老師收拾幾身換洗衣物再送過來。
南笳讓陳田田跟她一塊兒先回去,拿上她家的鑰匙先去休息。
醫院離解文山的書店很近,打個車十分鐘。
書店裡燈還亮著,門沒鎖,不過「暫停營業」的牌子掛了出來,興許是鄰居幫忙掛的。
南笳進屋去,收拾了衣服、洗漱用品和身份證、醫保卡,走到門口,又折回,從書架上拿了兩本書。
關了燈,走出門,正準備鎖門,忽聽身後有停車聲。
轉頭,隔著夜色,眯眼一看,路邊停了輛黑色轎車。
車門打開,後座下來一個陌生男人,白衣黑褲的簡單打扮,但身形修長孤拔,戴一副細框眼鏡,有種清孑嶙峋的氣質,與這市井之地有點格格不入。
男人目光十分平淡,「解老師已經休息了?」
南笳問:「您是過來買書的?」
「不是。路過這兒,方才看店裡還亮著燈,順便過來打聲招呼。」
「您是……」
「解老師的學生。」
「那不巧,解老師住院去了。」
男人頓了頓,「什麼時候的事?」
「就剛剛。急性心肌梗死。送醫院及時,沒大礙。就是要住幾天院。」
男人看了她一眼,「你送的醫院?」
南笳點頭,「我是解老師鄰居。您要去醫院瞧瞧嗎?或者給解老師打個電話,再約時間?
男人往她手裡提著的東西看。
南笳意會,「哦,這都是給解老師的東西,準備去趟醫院給他送過去。」
男人往旁邊邁了一步,伸手,拉開了車門,「麻煩帶我過去看看。」
南笳猶豫一霎,還是上了車。
後座很寬敞,南笳在左邊的座位上坐下,將裝東西的兩隻紙袋放在自己雙腿上。
空間十分安靜。
南笳拿餘光去看身側的男人,他蹺腿閒散坐著,手肘撐在車窗框沿上,轉頭看著窗外,窗戶玻璃映出一張沒有半分情緒的臉。
南笳嗅到空氣裡有一股冷冽的雪松味,過足的冷氣把這車廂營造得像在冬日。
她沒有出聲,而顯然男人也認為兩人沒有互相認識的必要。
一路沉默著到了醫院。南笳率先推開病房門,走過去確認解文山是醒著的,低聲說:「解老師,您有個學生過來探望您。」
解文山偏頭看一眼,很是驚訝,手掌撐著床沿想坐起來,聲氣虛弱地說:「濂月?你怎麼來了?」
那男人幾步走過去,伸手按了按解文山肩膀,「您躺著,好好休息。」
解文山強濟精神地笑了笑,「今天都這麼晚了,怎麼不明天再抽空過來。」
「正好順路。」男人沒多解釋什麼,伸手拿起床頭柜上的住院單瞧了瞧,「要住幾天院?」
「一周多。」
「我叫人安排護工照顧您。」
解文山侷促極了,「不用,這太麻煩你了。」他瞧了瞧南笳,那表情有點像是期望她能說點什麼。
南笳便說:「我陪護就行了。」
男人甚至都沒看她一眼,只問解文山:「您覺得呢?」
他說話一直是平聲靜氣的,但無端予人以壓迫感。
南笳微微聳聳肩,瞧一眼解文山。
明顯解文山已經向他這位學生妥協了,囁嚅片刻後說道:「那都聽濂月你安排吧。」
一會兒,有護士過來叫他們早些離開病房,時間太晚了,病人都要休息。三人間沒有陪床條件,也用不著,每隔一小時就有護士過來巡邏,出不了什麼事。
如此,南笳便對解文山說:「解老師,那我先走了,明早再過來看您。——哦,給您帶了兩本書,精神好些的時候可以看看,打發時間。」
解文山笑笑,「還是小笳你了解我。」
立於一旁的那男人,似乎沒有要走的意思,仿佛是要跟解文山單獨再說兩句話。
南笳沒再說什麼,走出病房,順手掩上了門。
醫院大門外,車流稀疏,長明的路燈也顯出幾分睏倦。
南笳有種心有餘悸的感覺,從提包裡拿出煙盒和打火機,點了一支煙。
她穿一身黑色,吊帶上衣、皮裙和馬丁靴,濃妝,散著一頭捲髮,適合喝酒蹦迪的裝扮。
是直接從酒吧回來的,遇上了解文山這檔子事,衣服都沒空換。
深更半夜在路邊徘徊,又是這樣一身打扮,叫人誤會也難免——南笳正抽著煙,餘光裡瞧見前面一輛明黃色的跑車駛了過來。
跑車一個急剎,停在她跟前,車窗落下,駕駛座上有個男的偏頭朝她這邊望,吹了聲口哨,「美女去哪兒?請你喝酒?」
南笳懶得理。
那男的陰陽怪氣地「喲」了一聲,「那要不直接開個價?」
南笳咬著細細的煙,騰出手,衝對方比了個中指。
那男的非但沒被勸退,反而似乎更來了鬥志,笑著罵了句「操」,又說:「我誠心的,美女只管開價。」
南笳說:「我口味重。」
男的笑得意味深長,「多重?」
南笳:「背後是醫院,瞧見了嗎?」
「醫院怎麼?」
「我男朋友綠帽癖,在這兒住院呢。要不我給你開個價,咱倆去他的病房裡當他的面來一場,好不好啊?」
男的臉色陡變,「神經病。」
一踩油門,溜得比什麼都快。
南笳不過掀了掀眼,神情平淡地繼續抽菸。
手機響起微信提示,她摸出來看一眼,狀態欄裡數條未讀,一時都懶得點開看。
抬眼朝路邊張望,想瞧瞧有沒有空計程車,一轉頭卻微微愣住——
前方有臺自動售貨機,解文山的那學生站在那旁邊,手裡也拿著一支煙。
他在那兒多久了?
南笳眯了眯眼。
路燈是暖黃的,但奇怪的是,他在暖色的調子裡人顯得更冷,瞧過來的目光也毫無溫度,只有一種似乎超脫於萬事之外的淡漠。
男人問,「貴姓?」
南笳有點納悶他突然而來的好奇心,「南。南笳。」
男人向不遠處投以目光,「送南小姐一程。」
南笳順著他的目光看去,他的車停在那兒。
那黑色轎車品牌很低調,車牌號卻不低調,a字打頭,後頭接續一串連號的數字。
南笳笑了聲,這人,甚至不屑於同她同等地自我介紹一句?
「那請問您貴姓?」
男人瞥她一眼,這才說:「周。」
實在是一個很好看的男人,是她日常生活中極少會碰到的那一種類型,她覺得文學作品裡動不動形容人像石膏像,很土很沒有想像力,但細看周濂月又想不出別的什麼形容詞。
也像是冷澗深雪。
總歸都是些沒有活人氣息的東西。
不管是他車牌號昭彰的非富即貴,還是他這性格,南笳都不大敢深入跟他打交道。
「周先生,謝謝你好意。不過我自己已經叫了車。」
周濂月眼鏡之下的目光平靜無瀾,並不再邀請第二次,收回目光,轉身朝停車的地方走去。
南笳解鎖手機,叫了一輛車。
等車來的時間,走到了周濂月方才所站的地方。
自動售貨機亮著燈,裡頭飲料瓶琳琅滿目地陳列,有種清涼的潔淨感。
南笳彎腰研究了會兒,伸手按了一罐可樂。
可樂罐滾落下來,落在取貨通道。
南笳俯身拿出來,吊帶的肩帶順著肩頭往下滑落些許,她直起身後,不甚在意地拉了一下。
她咬著煙,一手拿著易拉罐,一手扣開了拉環,「砰」地一聲,噴出氣體。
仰頭喝了一口,忽然直覺有人在看她。
抬眼看去,前方,周濂月的車正飛馳而過。
車窗半落,她與周濂月的視線一霎交匯,又倏然飛逝。南笳到家已過凌晨。
陳田田在她的舊沙發上等得睡過去,聽見敲門聲才迷迷糊糊爬起來開門,打著呵欠問她:「醫院那邊處理完了?」
「嗯。你洗過澡了?」她看陳田田穿的是她的睡衣。
「洗過了,你也趕緊去洗了睡吧。」
「好。你先去吧。」
南笳脫了衣服,穿著內-衣去浴室卸妝。
她租的是胡同裡的四合院,房東重新裝修過,設施倒是齊全,不過條件也就那樣,門歪窗斜的,花灑老壞,馬桶老堵。
這些小毛病都能將就,主要是住習慣了,也喜歡這附近便利的生活條件,加之離解文山那兒近,有個說話的人,不那麼孤獨。因此畢業之後就一直住在這兒,沒換過。
南笳拿蘸了卸妝水的化妝棉敷在眼睛上,聽見陳田田在臥室裡喊她:「笳笳,你有語音電話。」
南笳扔了化妝棉,抽一張洗臉巾胡亂擦了一把臉,飛快走回臥室。
手機電量只有不到5%了,還在盡職盡責地站最後一班崗,南笳說:「早知道上個月不換新手機了。」上個手機電量低於10%的時候會隨時在任何一個節點突然關機。
「什麼?」
「沒。」南笳將手機調成靜音,丟到一旁去,「你睡吧。」
「誰打的?」
「鄭瀚。」
「還纏著你呢?」
「嗯。」
「你不是已經拒絕他了嗎?」
「話說輕了他裝傻,說重了我又不敢,人大人物我惹不起,撕破臉最後倒黴的還是我自己。」南笳妝卸了一半,臉上黏糊糊的很難受,「你快睡吧,不用管我了。」
等卸妝完,洗完澡,南笳躺在床上,累過頭了卻毫無睡意。
一旁陳田田睡得很香,偶爾換成仰躺的睡姿,發出輕微的鼾聲。
南笳爬起來,到門前的臺階上坐著抽了支煙。
四四方方的院子,框一方暗沉沉的天空,只有遠處一盞路燈越過圍牆,發出螢火蟲似的一點光芒。
-
隔天早上,南笳沒叫醒陳田田,由她睡到自然醒,自己買了些水果,去醫院探望解文山。
到了病房,解文山睡的那一床卻是空的,一打電話才知道,他調到vip病房去了。
南笳找到新病房,解文山穿藍色條紋病號服,靠坐在病床上,面色幾分憔悴,但精神似乎還行,正在翻南笳給他帶的書。
南笳問他:「吃過早飯了?」
解文山把書往旁邊一蓋,笑說:「吃過了。」
「護工給您送來的?」
解文山點頭。
南笳玩笑道,「您這位學生,一定來頭很大吧?」一句話就能把人換到vip病房。
一提到周濂月,解文山便顯出三分的侷促,「興許是吧,反正是我平常打不上交道的那一類人。」
「怎麼會,多少達官貴人找您求賜墨寶,他不至於能比這些人還厲害。」
「我也說不清他具體是做什麼的,一直也沒問過。」
「不是您學生嗎?」
「學生和學生也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解老師不細說。
南笳笑笑,「他是您剛收的?您的學生我能數個七七八八,倒是第一次見這位。」
「那不是。我跟他認識也有三年了。」
南笳認真想了想,「我好像真沒見過他。」
「可能是不湊巧。」解文山明顯不想多聊,換了話題,「對了,小笳,我還沒謝謝你,要不是你……」
「別煽情,您知道我討厭這個。」
解文山笑了,「那我不說了。」
南笳跟解文山認識有四年多了,解文山年過六旬,終身未婚,膝下無兒無女,也沒見有別的什麼親人。
起初南笳覺得人怪可憐的,這麼一孤寡老頭兒,獨自守著這麼一爿小店。久了才發現,跟解文山來往的那些人,各個有來頭。後來一時興起去搜他的資料,才知他曾經是書法協會的副主席。
北城就這麼一神奇的地兒,再怎麼不起眼一老頭,也有可能是大隱隱於市的掃地僧。
解文山很照顧南笳,念及她一外地姑娘,在北城打拼不容易,逢年過節,總會叫上她去他那兒吃飯。
解文山博覽群書,性格儒雅隨和,兼有三分風趣。做飯手藝也好,一手紅燒魚,不比外頭的高級餐廳差。
能蹭飯,又能聽解文山講古,南笳簡直求之不得。
南笳在北城的朋友很多,但真正稱得上像是親人的,解文山是為數不多的幾個之一。
南笳從自己給解文山帶的水果裡,拿了只橙子出來,拖開椅子在病床旁邊坐下,邊剝邊說:「對了,跟您說個事兒。」
解文山看她。
「我上周不是跟您說,我接到了一個角色,不久就要進組麼?」
「這事兒……」
「黃了。」南笳很平靜。
解文山比她更失望,「不都籤過合同了,這也能反悔?」
南笳笑笑,「人家也是混口飯吃,不想惹麻煩。」
「這種不講信義的劇組,不去也罷——小笳,你別失望啊,以後肯定多的是機會。你業務能力這麼強,大紅大紫的時候還在後頭呢。」
「但願吧。借您吉言。」
說著話,南笳手機響起來。
她騰出手拿出來看一眼,還是鄭瀚撥來的。她把剝好的橙子掰成兩半,遞到解文山手裡,扯了張面巾紙擦擦手,「我出去接個電話。」
南笳拿上手機走到病房外,順手掩上門。
電話接通,鄭瀚的聲音裡帶了點兒宿醉未醒的含混:「哪兒呢?我來接你,一塊兒吃早餐去。」
南笳笑笑:「醫院裡。我有個朋友病了。」
「搪塞我也不帶拿你朋友開玩笑吧?」
「真的,要不鄭少撥視頻過來看呢?」
「那你自己說個時間——南笳我告兒你,欲擒故縱那也得適可而止,多了就沒意思了啊。」
南笳在心裡罵髒話,語氣倒還是笑嘻嘻的,「我哪兒敢對鄭少欲擒故縱呀——下周?下周我朋友就出院了。
-
一周後,解文山恢復得不錯,如期出院。
這期間,南笳倒沒再見過周濂月。
解文山出院之後就在店裡將養,搬書理書的這些笨重的活計,南笳有空就去幫他做了,解文山只用幹些不費事兒的,倒也不影響書店的正常經營。
老實說,書店生意也就這樣,賣的都是些佶屈聱牙的老古董,除了老主顧,根本沒什麼新客和散客。南笳有別的事情煩心——鄭瀚下了最後通牒,她敷衍不過去了。
-
周濂月在朋友的場子裡,再次碰見南笳。
屈明城新開一座莊園式度假酒店,吃喝玩樂一應俱全,只對會員開放。
周濂月應他的一再邀請,過去捧捧場。
他倆打小的交情,生意上關涉不大,反倒能成為較為純粹的朋友。
屈明城親自到門口去接上周濂月,一邊帶他往裡走一邊介紹,這裡頭的裝修一水日式風格,那是溫泉,那是咖啡廳,那是娛樂中心……瞧見庭院裡那棵槭樹沒有?花大價錢從日本移植過來的,等秋天一到,紅得那叫一個漂亮。
他見周濂月不甚有興趣,便問:「老周,你有什麼想法?我這地方還算地道?」
周濂月說:「多折騰這些花架子,你賠得更快。」
屈明城笑說:「這回我還真不信邪。」
他倆穿過走廊,屈明城一停,往一旁的一間房裡瞥了一眼,裡頭有個他的熟人,「老周你先去茶室坐會兒,我打聲招呼再過去找你。」
走廊盡頭便是茶室,很地道的日式風格。
周濂月走到窗戶邊上,鬆了松襯衫領口,點了支煙。
抽了兩口,忽聽外頭庭院裡有說話聲。
屈明城高價移植的那棵槭樹下,有兩個摟抱在一起的身影。
周濂月挺厭煩這些事兒,剛準備從窗戶邊離開,那其中說話的女聲卻叫他腳步一頓。
隔了一段距離,夜色又暗,面容看不清,但聲音很耳熟。
是熟悉音色,卻不是熟悉語調,那黑暗中的輪廓,似乎是男的雙手緊緊摟著那女的的腰,而女的帶笑的聲音甜膩、虛浮極了,像盛了一碗蜜,蒼蠅下腳都嫌黏重。
男的明顯喝了酒,說話大著舌頭,語氣更輕浮不過:「今兒跟我走?你找藉口的次數夠多了,我夠能忍你了。」
女的便以那甜膩的聲音哄道:「哪有故意找藉口,真是因為朋友生病了。你看,今天不就來赴約了嗎?」
男的笑了一聲,「那跟不跟我走?」
「我能提個條件嗎?」
「能啊。我是那種小氣的人?只管提!我們鄭家你還不知道,什麼門路沒有。」
女的笑著附和兩聲,「那鄭少知道我是演員吧?」
「知道。你們那小劇場叫什麼來著?下回給我兩張票,我去瞅瞅。」
「有機會一定請鄭少去捧場——這不是前陣子我接了個戲,我以前得罪過人,劇組怕事兒,就換了個人頂上去。鄭少有辦法幫我拿回來嗎?」
「這還不容易?我不就做這行的嗎?那我要是答應你了,你今晚……」男的向女的湊攏,一時壓低了聲音。
女的笑得花枝亂顫,「那當然。鄭少想做什麼,我都奉陪……」
男的聲音都啞了兩分,兩手在女人的腰間逡巡,一邊問道:「那你說說,你得罪了誰?」
「邵家。」
男的動作肉眼可見地一滯,「……哪個邵家?」
「北城有幾個邵家?」
男的的以極快的速度一把推開了女的,「南笳,你玩兒我是吧?」
「不是鄭少自己說的嗎,有什麼難處都可以提,這就是我的難處呀。」女的語氣十分無辜。
「……你真得罪了邵家?」
「我敢開誰的玩笑,也不敢開邵家的呀。」
男的不說話了,頓了一會兒,退後一步,罵了幾句髒話,轉身氣急敗壞地走了。
黑暗裡,剩下的那身影一動也不動。
片刻,她蹲下身,一陣窸窣的聲響的過後,黑暗裡突然燃起一捧火光。
周濂月隨手將煙按滅在了菸灰缸的碎米石子裡,朝通往庭院的那扇門走去。
日式的庭院,步道由鵝卵石砌成,沿路地燈昏暗,唯獨那樹下的火光亮得很。
空氣裡有燒焦的氣味,十分明顯,怕是過一會兒,就有人要過來滅火了。
周濂月加快了腳步。
許是聽見了腳步聲,南笳轉頭看了一眼。
火光將她照亮,她穿著一條黑色緊身連衣裙,低胸,長度只到膝蓋以上,妝容比頭一回見她時更濃,但似乎故意有點沒好好化,顯得十分俗豔,與她身上這條既露大腿又露-胸的連衣裙一樣。
但她目光卻像清霜一樣的冷。
和方才黑暗裡曲意逢迎的判若兩人。
她手裡捏著一包煙和一隻打火機,目光平靜,說不上有什麼情緒。
而只看了一眼,她就轉回頭去。
周濂月站在她身後,看向被燒著的東西,那像是份文件,有彩色記號筆塗畫的痕跡,細看內容格式,挺像劇本。
盛夏的夜裡,空氣依然溽熱,燃燒的這一叢火,更加劇了這份熱度。
他暴露在外的手腕和手背,能直觀感受到這熱浪,一息一息地撲上皮膚。
紙張卷邊、燃燒、焦枯、漸次成為灰燼。
燒到到最盛的時候,南笳細長手指將煙盒一揭,拿出一支,將菸頭湊攏那火焰,點燃了。
拿辭藻與句章點菸。
一種毀滅感的浪漫,像詩人做的事。
周濂月這時沉緩出聲:「你找錯了人做交易。」
南笳沒什麼表情。
「鄭瀚家裡經營邵家下遊配套產業,他招惹誰也不敢招惹得罪過邵家的人。甚至騙都不敢騙你,怕惹一身腥。」
周濂月語速不急不緩,完全是陳述客觀事實的冷靜聲調。
南笳挺意外他有耐心同她解釋這麼多,可她並沒有耐心同他解釋,她根本也沒想跟鄭瀚做交易。
她笑了聲,就這麼抬眼向上盯著周濂月,刻意拿那泛著甜膩的語氣笑問:「那周先生就是那個對的、能做交易的人?周先生就敢招惹邵家麼?」
周濂月頓了似乎都不到兩秒鐘,眼鏡後清冷的目光掃她一眼,「有何不可?」
南笳一愣。
他的話,措辭到語氣,都有不容置喙的說服力。
南笳不喜他居高臨下的審視,當即站起身,但身高差距在那兒,並沒有使這被俯視的壓迫感有所消減,於是又下意識地後退了半步。
周濂月看她,「不想要?」
南笳緩緩地呼吸片刻,又笑了笑,「代價是?你給得起我想要的,我不見得給得你想要的。」
「沒有給不給得起——」周濂月看她的目光十分安靜,讓她想到某一天劇場演出結束,回家路上,在深夜的路口抬頭看見的一輪幽冷的月亮,「只有願意不願意。」坦白說,南笳從來不信「美而不自知」這句鬼話。
她太知道自己長得還不賴。
出去吃飯,十回有九回被要微信不說,她是北城電影學院那一屆的藝考和文化課雙第一,一貫不苟言笑的班主任都曾對她報以「星途坦蕩」的期許。
十九歲拍了自己的第一支廣告,國民品牌的橘子汽水,在一些盤點古早廣告的剪輯視頻裡,她露臉的瞬間彈幕鋪滿,都在問這是誰,我要一分鐘內得到她的全部資料。
——七年前算不算古早呢?
但無論如何,那些風光已是七年前的事了。
這個圈子裡,美貌稀缺嗎?稀缺也不稀缺。稀缺是相對於大眾層面,可當她身處的環境各個都是俊男靚女,她不會覺得長得好看是一件多了不起的事。
南笳說不出周濂月的來歷,但也知道是金字塔頂端的人。
美貌於他這樣的人,是最最最不稀缺的東西。
十九歲她會信,一定信會有男人對她一見鍾情赴湯蹈火。
可現在是二十六歲的她。
二十六歲的南笳,早就被蹉跎得沒有一點所謂「美人」該有的自傲和驕矜。她照鏡子時自己都能看出,程式化的笑容有多膩味。
可如果周濂月不是圖她的外表,又圖什麼?
總不會是圖她的靈魂?
她自己想想都要發笑。
南笳沉默的時候,那叢火漸漸地燒完了。
她剛要開口,周濂月卻先一步截斷她:「不用著急給我答覆,你考慮清楚。」
他轉頭睨了一眼,因為茶室那頭屈明城在叫他。
他先沒應,又轉過頭來看眼前的人,「我叫人送你回去。」
南笳不想逞強了,今晚真叫她噁心透了。
鄭瀚噁心,自己也噁心。
於是沒有拒絕周濂月的好意。
周濂月給司機打個了電話,而後向停車場的方向一指,「我車你應該認識。」
「謝謝。」南笳說完,又看了看地上那堆灰燼。
周濂月說:「不用管了。我叫人來打掃。」
車開到胡同口,南笳瞥見解文山的書店還亮著燈,她沒過去打招呼,下車之後就直接回家了。
到家以後,給陳田田發了條消息,告訴她鄭瀚的事情已經解決了。
陳田田請她出去吃夜宵,她說再說吧。
-
南笳黃掉的那演網劇的機會,是話劇團背後的大老闆,丁程東介紹的。
丁程東做生意的,一個沒什麼文化的土老闆。十年前娶了個演話劇的老婆,後來老婆難產,大人小孩兒都沒保住。
年景不好,文化相關的產業都挺難存活,丁程東亡妻待的那話劇團也快解散了,攥手裡的幾齣劇目都要賣給別人。
丁程東跟他老婆談戀愛那陣沒少在話劇團裡鬼混,為留住點兒兩人的共同回憶,丁程東一咬牙就盤了這劇團,拉扯至今,後續又拉了些投資,聘了個專業的主理人。前些年一直在賠錢,如今勉勉強強收支相抵。
南笳是畢業兩年後加入進來的,起初只演名字都沒有的配角,慢慢的也混到了主角,還是a角。
丁程東老婆跟南笳老家一個地方,都是南城人,因為這,他一直挺照顧南笳。
有一陣團裡風言風語,傳得很難聽,丁程東揪出幾個起頭的,直接跟人幹了一架。
他撂了話,這輩子不會有除他老婆之外的其他女人,不然叫他做生意賠到底掉,出門給車撞殘廢,幾把爛光。
拿命-根子發這種毒誓的,大家還真沒遇到過,都被震住了,往後再沒傳過這種流言。
私底下,丁程東挺煞有介事對南笳說:南笳,我對你完全沒想法,你這種小丫頭片子我一點興趣都沒有。要是你對哥有興趣,那哥只能提前對你說句抱歉了。
南笳哭笑不得。
丁程東認識些做影視投資的人,也輸送了團裡不少演員去拍戲,這回這部網劇雖說是小成本,但主創團隊都挺有誠意,他就給南笳爭取到一個演配角的機會。
他一直覺得南笳很有資質,應該往更大的平臺去。不就是得罪個人嗎,那人還能時時刻刻盯著不成?這事兒不就是,餓死膽小的撐死膽大的。
然而,可惜,南笳得罪的人就是這樣手眼通天,放話說要封殺她,就一定不會叫她在任何正兒八經成規模的影視劇裡露頭。
南笳請丁程東吃鐵板燒賠罪,辜負他的一番安排。
丁程東嫌棄鐵板燒不過癮,到嘴的食物有一茬沒一茬的,還不如胡同裡找家燒烤店,三十串羊肉下肚,什麼都舒坦了。
南笳吐槽他不識貨,這新開的網紅店,知道號多難排嗎?我託了多少關係才訂到的座。
插科打諢過才進入正題。
丁程東說:「南笳,你沒對不起我,我就只幹了點牽線搭橋的事。反倒我覺得挺對不起你的,要是哥混得再成功一些,指不定就不用叫你受這鳥氣。」
南笳笑說:「以我們凡人的資質,混得多成功都沒用。人家不用我,仍然是一句話的事。」
丁程東不知道第幾次問她:「所以,你到底怎麼得罪了邵家的人?」
南笳搖頭,「你不知道比較好。」
她拿起啤酒瓶跟丁程東碰杯,不想繼續聊這事兒。
她讓丁程東講點開心的,正準備聽他分享他上次差點被人訛了,一百萬買一紫砂壺的故事,忽聽有人叫她。
南笳回頭一看,是張很熟悉的臉,她本科時的同學莊安娜。
畢業後南笳就沒跟她見過,她現在混得馬馬虎虎,前陣子演了個蛇蠍美人,小火了一把,南笳看見她給新戲打廣告還點過贊。
莊安娜確認是南笳之後,流露出了強烈的鬥志,搖曳生風地走過來,笑說:「南笳?真是你啊!我都以為你已經回老家發展了。」她說話時目光在打量丁程東,可能以為這是南笳的男朋友。
南笳只能笑笑:「好久不見。」
「是挺久的,畢業以後就沒見過了吧?也沒見你拍戲。你現在還在做這行嗎?」
「不做了。」
「那做什麼?」
「沒工作。靠人養。」
莊安娜看向丁程東。南笳點頭,「對。就他。我老公。山西開煤礦的。」
莊安娜拖長聲音,意味深長地「噢」了一聲,「也挺好。做家庭主婦多穩定啊,不像我們,演員說出去光鮮,吃苦全在人後。」
南笳:「那要不你也嫁人?我老公挺多兄弟,也都是開煤礦的。可以介紹給你,我們做妯娌啊。」
莊安娜的表情像咽下一口蒼蠅。
南笳乘勝追擊,「你坐哪桌啊?要不過來我們一起坐,好好聊聊這事兒。」
莊安娜可是女明星,女明星是不會輸的,「不用。我跟李導約了要聊新戲,一會兒人就到了。你們慢吃,有空找我約飯啊。」
南笳笑說:「那你下周五有空嗎?」
莊安娜都慌了,好像生怕南笳狗皮膏藥一樣貼上去。
她朝門口張望,「李導好像到了,我去接一接。先失陪了。」
溜得好快。
丁程東早就憋不住笑了,「這人誰啊,至於你殺敵一千自損八百?」
「東哥你看過我橘子汽水的廣告吧?」
「看過啊,挺經典的。」
「那就是我當年最終面打敗她拿下的。」
「嗬,你還有這種英勇事跡?」
「可不是。」
這頓飯結束,散場時,丁程東問南笳,「最近和葉冼見過嗎?我聽說他要離開北城回老家了,這事兒是真的?」
南笳心裡一驚,「我不知道,他沒對我說過。」
-
葉冼的工作室在近郊的一個工業區改建的文化園區裡,那裡租金低,也不怕擾民。
純磚牆的建築,工業風格,各種管線直接暴露在外,有種粗獷的美感。
夏天的時候,外牆上那一叢爬山虎生得鬱鬱蔥蔥,南笳每回過去都要在外面觀賞好一會兒。
一樓的大廳裡,堆放著各式各樣的樂器,南笳進門的時候,葉冼正在擦拭吉他。
不是錯覺,她真感覺出葉冼有要走的跡象,平常他的工作室亂得無處下腳,今天卻收拾得一乾二淨。
她懷疑葉冼在清點工作室的資產。
南笳笑問:「葉老師,做掃除呢?」
葉冼手裡動作一停,抬頭看了看,笑了,將吉他往旁邊的皮沙發上一放,起身,「怎麼有空過來。」
南笳玩笑:「過來看看葉老師有沒有好好吃飯。」
葉冼笑了,「那你吃過晚飯了嗎?」
「沒呢。」
「我這兒有中午打包的剩菜,要不介意……」
「不介意不介意。有酒嗎?」
「有啤酒。」
南笳高興地跟在葉冼身後,進了廚房。
所謂廚房,是以前車間的水房改造的,葉冼在裡頭支了一張桌子,放一臺微波爐和電磁爐。電磁爐用到的機會都很少,平常多半只用微波爐熱一熱便當。
葉冼從冰箱裡拿出打包盒,一一丟進微波爐裡,設定時間,啟動。
正當黃昏,濃鬱的霞光照進來,使站在靠窗那一側的葉冼,變成了一道清瘦的剪影。
南笳背靠著那張桌子,手掌撐在桌沿上,輕聲開口:「我聽說,你準備離開北城回老家了?」
「嗯。」
「發生什麼事?」
葉冼抬手揉了一把頭髮,「……我爸生病了。癌症。」
葉冼在北城混了這麼多年,卻幾乎沒存下什麼積蓄。
錢花在買樂器,天南地北地採集自然中的音色,以及貼補比他更慘澹的朋友……
和不稀缺美貌一樣,北城也不稀缺才華,他用心,才華橫溢,但始終欠缺一個機會,他能做那麼好的音樂,卻一直只能給他人做嫁衣裳,比明珠蒙塵更意難平。
南笳看著他:「要多少錢?可以湊的,我們幾個朋友雖然混得不算好,但……」
葉冼臉色少見的幾分疲憊,「南笳,不純粹是錢的事。我覺得我應該回老家了,你知道,過了今年我就三十……」
南笳太明白了,所以來之前打的那些勸說的腹稿,完全無法開口。
南笳一直將葉冼視作精神上的燈塔,只要一想到追逐遙不可及的夢想的人中間,還有一個比她純粹、比她淡泊、比她堅韌的存在,她會備受慰藉。
可這對葉冼不公平。
他應該發大財,應該揚名立萬,不應該只清貧地做某一個人,或者某一些人精神世界的偶像。
更不應該,在北城做一粒無足輕重的塵埃。
他們沉默了好一會兒,直到微波爐「滴」的一聲。
葉冼回神,打開微波爐,將下一份打包盒放進去。
南笳情不自禁地伸出手。
夕陽將他照得倒影折落在桌面上。
她意識到她伸出手,是想要去觸摸他的影子。
-
不管復盤多少次,南笳都會承認,她找解老師要周濂月的電話號碼時,沒有過多的心理掙扎。
電話接通的那一瞬間,也平靜不過。
她問:「我是南笳,還記得我嗎?」
周濂月說:「嗯。」
她問:「上回你說的話,還作數嗎?」
周濂月說:「當然。」周五的演出結束,南笳喊上陳田田一道吃夜宵,順便找她打聽周濂月。
劇團新排的這齣沉浸式話劇叫做《胭脂海潮》,試演成功之後就正式提上日程,變成往後每周五到周日的固定劇目。
每次演出結束之後,總有一些劇迷在劇院大門口蹲演員要籤名。
南笳他們都很隨和,讓籤什麼就籤什麼。
反正攏共也就那麼七八個劇迷。
有個學生模樣的小姑娘拿著《胭脂海潮》的海報請南笳籤字,全程拳頭半遮著臉偷瞄著南笳,小聲地說:「姐姐你好漂亮。」
南笳笑說:「謝謝。你也很漂亮。」
小姑娘拿到籤名之後暈暈乎乎地走了。
陳田田走過來一把摟住南笳肩膀,「真有你的,男女老少通吃。」
劇場外就有燒烤攤,大家常常過來擼串。
他們搞先鋒話劇的,大部分穿著打扮都挺「亞文化」,在外人看來喪裡喪氣,又不倫不類,他們好像自發形成了一層屏障,與其他吃燒烤的人完全地區隔開來。
南笳跟陳田田單獨坐一張小桌。
她開了罐啤酒,遞給陳田田,「跟你打聽個人。」
「誰?」
「周濂月。」
南笳所在的劇院,實話說,很窮,但混在裡面的,不全是她這樣一事無成的北漂,也有真正家裡不愁吃穿,只為投身藝術的人。
陳田田就是這樣的人。
陳田田父母經商,在北城是毋庸置疑的中產以上。家裡還有個哥哥,做金融的;有個姐姐,幫著家裡做事。作為老么,家族生意延續的壓力遠遠落不到她頭上,她就專心致志做自己的先鋒戲劇,當編劇,當演員。她還有個男朋友,青梅竹馬,好了好多年了。
南笳在網上搜過周濂月——其實她之前一直以為周濂月的名字寫法是「周連嶽」,問解老師要電話號碼時才知是這個「濂月」。
聯繫他的形象,覺得無比契合,甚至覺得世界上再也找不出來另外兩個字能比這更襯他的氣質。
網上關於他的資料實在太少,只出現在某投資基金會官網的合伙人名單裡。
陳田田的交際網絡比較廣,興許知道關於周濂月的信息。
陳田田的第一反應是嚇一跳,「怎麼問起這人?你認識他?」
「他是解老師的一個學生。」南笳選擇隱瞞了一些內容。
陳田田笑說:「我看解老先生才是真大佬,周濂月這樣的人都能是他的學生。」
「所以周濂月什麼來頭?」
「他本人是做投資的,你現在能數得出來的市面上成功的科技公司,基本都有他那基金會的融資。更重要的是,他背後的靠山,跟咱們不是一個階層,是真正的……你懂吧?」
南笳瞭然,「那他本人呢?」
「本人什麼?」
「私生活這些。」
陳田田喝著啤酒,看了南笳一眼,「他人很低調,私生活這方面的傳言不多,大體上應當不是那种放浪形骸的紈絝子弟,不然早就名聲在外了。」
「他結婚了嗎?」
「結了,還是英年早婚。」陳田田盯住南笳,忽然意識到什麼,「笳笳,是不是瞞我什麼事了?」
南笳將菸灰撣進盛了半杯茶水的一次性茶杯裡,「田田,你覺不覺得,世界其實就是一個大賣場。什麼都能販賣,價值、尊嚴、靈魂、自由……只看是不是找對了買家,是不是有人出得起價。」
陳田田打量南笳良久,一時欲言又止,「我家不是做生意的嗎?我爸告訴我,買賣的第一要義是可以吃虧,但不能虧本。」
南笳笑笑。
虧不了本的,她相信那一定是個慷慨買家。
-
南笳和周濂月約定見面的地方是周濂月定的,不對外開放。
周濂月派車去接她,被她婉拒。
她自己打了輛車,遵照周濂月的吩咐,到地方以後給他發了條消息。
大門緊閉,越過白色圍牆,只能看見黑瓦的屋頂。
沒一會兒,大門「吱呀」一聲被推開,一個穿正裝的男人走了出來,探頭問道:「南小姐?」
南笳點頭。
「我是周總的助理,我姓許,你可以叫我小許。」許助把門推得更開,「請進。」
一段石板路,兩側是清澈水池,倒映天上即將西沉的落日。石板路盡頭是一幢迭層的新中式建築,白牆黑瓦,大面積的落地玻璃,整體風格素雅又低調。
進門以後,許助帶南笳穿過一段走廊,往東走,最後進了一間茶室。
深褐色茶桌形狀不規則,像是剖開的整段老木頭,只上了一層木蠟油。
許助叫南笳少坐,周濂月片刻就來,說完就匆匆地走了。
一會兒,有個著一身工作服的阿姨,步履緩慢地走過來,提著一小壺茶水,給南笳斟了一杯,緊跟著也走了。
許助所謂的「片刻」是將近四十分鐘。
南笳以無比的耐心等在這裡,看著窗外天光一寸一寸變暗。
她坐的位置望出窗外能看見山,圓而紅的夕陽已經落下去一半,等它整個地墜到了山後面,茶室陷入一種荒寂的昏朦。
又過了一會兒,燈光忽然齊齊地亮起來。
不單是茶室,是整幢建築,所有的窗戶,一瞬間亮起。
像一種叫人心緒不由翻湧了一下的儀式。
周濂月是在燈亮後不久來的,腳步匆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