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連載二十九(長篇小說連載49小醉沱江)
2023-06-01 04:24:57
長篇小說連載二十九?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這種話聽起來有些不吉利」,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於長篇小說連載二十九?跟著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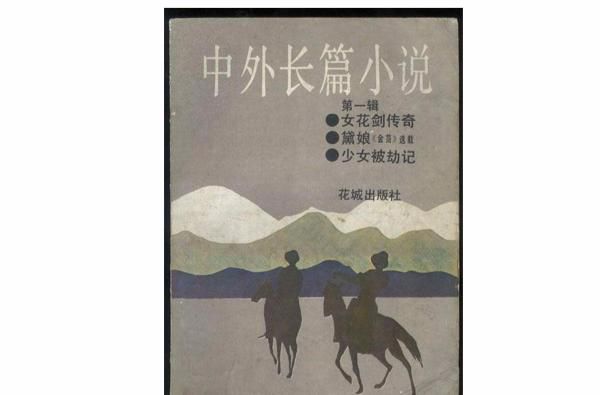
長篇小說連載二十九
大大地鬆了一口氣。
「這種話聽起來有些不吉利。」
「你每次發來給我的簡訊我總是翻來覆去看好多遍。」
他不停嘴(討厭得要死)催促侏儒朝那個(看不見的)方向走。(難道看不出來兩人彼此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先過橋,再往右拐,走在爬坡路上。板板車和小貨車停放在馬路邊賣蘋果、碰柑、香蕉、柚子和各種蔬菜什麼的。一個男子大聲吆喝。一個乞丐賣唱。夜市攤正在陸陸續續擺好。華燈初上,五彩斑斕,亮得甚至不肯把城市犄角旮旯遮擋半點。包括從哪裡傳出來電喇叭音樂,五味雜陳,合奏交響樂,所有的這一切,都像是催命鬼,短暫使他倆陷入迷茫。她雙腿得不到大腦的支配,朝魔法師所指引地方走去。那時候街邊小商店鮑勃•迪倫的歌聲再次響了起來。他還最後一次對她起過殺心,那是陳厚井死(2000年他三十三歲)之前兩個月的時候。這次他明知那種野菌有毒,卻聲稱是難得的好菜。
兩人在附近松樹林中做了愛(她喜歡)以後,陳厚井也公開把毒菌摘了回家。
他倆在出租屋自己弄晚飯。
菜刀把菜板故意弄得啪啪啪(是不是聽起來像……),啪嗒啪嗒,有點兒居家過日子的味道。他陰險地衝著侏儒笑了。這樣,惡作劇逐漸都成了常態,莫非還用得著仔細回味。噢,額頭上都有皺紋了。
還有那些細米粒兒汗珠。
擦一把汗,她遞塊毛巾過去。
「簡直好吃得不得了。」他對她說。
光陰荏苒,時間已經是2000年,好快!說起來也怪,他倆居然出人意料地同時感到一陣「身體不適」。兩盤菜裡,或者是喝的湯裡好像有人放進去了某樣東西,味道兒怪怪的,舌尖還發麻。她原話說就是有一股腥臭。結果兩個人都沒中毒,因為那頓飯,幾乎同時告訴對方頂好別吃了。非要吃別怪!話確實就是這樣說的。最後,他還假裝中了毒,倒在地上抽,發揮出他的演戲天才。「哪個膽大到真敢公開殺人呢。」他倆說,這話好像有種威脅成份。
「也別忘了,這算你幹的第二次。」
她說。侏儒撐起來打算告辭。
「你別忙!」陳厚井抓住她手指的意思恐怕就連自己都不甚明白。
他對她說:「我肯定不是心血來潮。」
「今天你太累了。」她說。
「我想,你今天沒有其他急事要辦吧?」
「沒有。」
「我想你留下。」
他說:「我想抱著你睡覺。」
當然也就留下了。陳厚井生前曾經去同性戀者澡堂……她驚訝地說真的是有那種地方?……嘴湊在耳朵邊講述,還比劃給她看,才不是你想像小偷小摸的樣子,見怪不怪,半公開化,差不多接近合法化了。他們膽子大得不得了。她說想去瞧瞧,可惜女的進不去。她緊張得嘴角肌都繃得那樣子僵,手指尖發抖。他只是去隔遠了聽,保持著適當的距離。當然瞅不清楚,燈光太暗,好像就是一些剪紙人,鬼頭鬼腦的灰暗影子。他們可沒啥好害臊的,顯得那么正大光明。聽男人與男人……對像更換頻繁……有些誇張,講話聲音如同陰曹地府。但他去僅局限於參觀,陳厚井不會跟同性產生關係,肉體碰出火花覺得噁心,更別說會有情感。總之太那個了,同樣就是個彼此嫖對方的場合,不排除有男多女少(指偽男同,加上不少偽女權主義者性格變得可怕,叫人寒心,找不到或對婚姻本身絕望、恐懼,經濟關係等諸多社會問題,退而求其次)這種因素,也有的是屬於基因突變,比較複雜。不小心到了那種地方陳厚井總覺得有點奇怪、噁心。
第一次去他確實吐了。
「我絕對不會允許任何人碰我,哪怕看都反感。」他有些自豪地說,「得用上絕招,就是衝他瞪眼睛,加大嗓門力度。」
他想可以粗聲惡氣的,對不管哪個。
也就是說一切膽大妄為進犯者。
「那你來幹嘛?」
天吶,一般情況對方不會或者說害怕問,都膽子小,並且無需回答。
「許多人像兔子。」他告訴她說。
難道,侏儒渾身發抖是懷疑他在扯謊。
陳厚井死在花旗竿街。
死之前(莫非他有預感)沒多久,有一次,陳厚井突然對侏儒說:「我倆乾脆結婚吧!」而且她差點就衝動答應他了。她有些猶豫,答應考慮。未來漫長歲月她常思忖,2000年如果不出那次車禍呢?
「我會不會過上另外一種人生啊?」
比較簡單的生活。
她並沒有指望已經算是她最後一任丈夫的姜抱回答。
2010年的時候她懷疑自己超過四十七歲了,與姜抱同居。
她想也許存在各種可能性。
姜抱才三十一歲。他倆不需要迴避以前許多事情。
她回憶起了2000年夏天陳厚井在他租房子住處強留下侏儒,然後,帶她上街吃頓便飯。她特別喜歡吃的菜是爛蒜椒香扒肥腸或乳汁肥腸,這種菜的主打材料都是豬大腸,要求洗得乾淨,去掉異味(她其實更喜歡多少保留一點點),在家做起來太費事。兩道菜做法腸子都要切成一釐米段,先蒸熟。調料有青、紅椒切碎、鹽、醋、醬油和蔥蒜,乳汁肥腸蒸前用鹽醃製,還加點番茄醬。湯汁都用燒熱的油加水製作而成,最後才把蔥花撒在面上。記得他當時說了這些話,蔣虹姐,真叫人不好意思啊,我少有請你去家像模像樣館子,我太窮,搞不好就失業,吃飯也只能在家將就湊合,沒辦法才找家便宜館子。他曉得花旗竿有家叫「達烏裡」的館子會做各種肥腸菜,也算是巧,街對門就有個公廁。她笑著說你惡不噁心啊!陳厚井本想事先對侏儒說明那一天正是他三十四歲的尾巴。但話到嘴邊咽了回去,落氣前才說怕她會給他買禮物。
「害得你手腳無措反而不好。」他說。
她哭成了個淚人。
「我才不想奉承討好你。」
「曉得你不會,」他說,「我這樣說罷了。」
隨後她光聽到急救車鈴聲。
「達烏裡」肥腸館雖然不是坐落在正街上,而門前的花旗竿街倒也熱鬧,人來人往,擠擠挨挨,車水馬龍,過街面本來有個地下通道但有不少人還是大搖大擺直插對門。她在想怎麼不直接叫「花旗竿」肥腸館而要叫狗屁「達烏裡」,這名字取得有點怪,是地名還是人名呢?陳厚井對她講什麼就沒太注意。不遠處,十字路口還有個站崗的中年交警,有個老婦人牽條阿里埃日犬和中華田園犬的雜種狗從門外路過,差不多就是條土狗,有點混亂,它還嗅了他褲管來著。堂子雖寬,客人也多,還有滿桌杯盤狼藉卻並不打算儘快撤離戰場的五六桌客人。有張桌子上三男兩女,女的抽菸,男的全在買醉,喝的還是烈性白酒,其中之一顯然已經喝過量了。她思忖,弄得夠麻煩的,這得瘋到哪種程度啊?三十歲花枝招展女人不知道她喝了多少,牛仔褲拉鏈拉開,她都渾然不察。也許她本就在故意挑逗。
「足見心不在焉,」侏儒想,「大庭廣眾又能有什麼作為呢?」
女招待把他倆帶拐左手安排在靠玻璃窗位子,所以她不光看到街頭風景,「後來我看到滿大街人都在奔跑。」多年後小矮人對姜抱說,她也不是這時候才發現陳厚井沒坐在對面,他說過去街對門屙泡尿,難道「達烏裡」沒有衛生間非得要去公廁。好像還聽到啪嗒腳步聲。
她奇怪地想起自己小時候和一個鄰居女孩……兩人都是十一歲,沒長……還有鄰居女孩八歲的妹妹在旁邊。
「八歲妹妹沒有參與。」
她顧自在玩布偶。
沒笑的中年交警由女招待在前面帶路走過來了。此刻,就站在她對面。
她飛快奔出「達烏裡」肥腸館大門,連撞兩個人。
街面紫紅色光斑不停地跳躍。
三十二
姜抱想起了早年間出在他們小縣城單家橋老街上的人和事。就拿那個老羅來說,記得他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姑娘,大兒子當兵去了,姑娘在老家好像已經出嫁為婦。姜抱仿佛從沒看見過她,或者,也許曾經見到過,但是沒有給他留下任何記憶。他的小兒子還在讀中學,不上課的時候兼做跑堂的,偶爾他也會代替父親送外賣。他和姜抱本來是在同一所中學讀書,就是同年級,並不是同在一個班,他倆沒「仇」,現在心平氣和回憶起來他倆早年間莫名其妙天生就存在某種敵意,與對方除了非說不可的話,當然是指兩家生意上的事(哪怕這種時候他好像也沒笑臉),記得他倆從來都沒有認真交談過。兩人看見對方都有點裝腔作勢。單家橋街上,好多的人,也不管是年輕的還是上了年紀的,多年後姜抱把大半人都忘乾淨了,反而是這個小飯館老闆和與之天生充滿了敵對情緒的小老闆讓他一次次回想起來難以磨滅。確實忘不掉。他那時候所想到,大約這是因為他倆都同樣失去了母親的緣故(其實姜抱離開縣城流浪前,飯館的老闆娘還沒出車禍喪命)。當然,姜抱母親是生病死的。
媽媽死的時候,小腹脹大如鼓,油亮閃光,他想像那裡面是臭哄哄帶一股腥味的濃血,甚至,猜出來那血的顏色,有一些發黑,有些黏糊糊的塊狀物。父親在後來還提到過老羅家的事一回。這個老羅又結了婚。他結婚後不再開飯館了,也許就在那次車禍後,他就早早地把飯店關張回鄉下種地去了。那時候姜抱正在廣東的一個吉他廠工作。他才剛剛站住了腳。
現在,有空閒來姜抱想起那個死掉(可能是一次意外)的老雞。
「小雯。雯兒,也許她是叫這個名字。」
僅姜抱一個人這樣喊她。
「你這個總是喜歡大驚小怪的酸臭小子。」她喊叫。
「老雞婆。」他罵。
「只怕你連毛都沒長吧。有東西x得出來不?」
「你想對老子胡攪蠻纏到哪樣地步!」
「別害羞嘛。老娘會拿破處紅包給你。」
噢,幹你這一行還有這種規矩的嗎?
「任何人的忍耐都是有限度的。」他漲紅了臉說。
「臉都紅齊頸子了還在裝。」老雞說。
「你住在哪裡?」
駱沙他們又在喝酒。姜抱不敢那樣喝的,他得保護嗓子。有人來叫他的時候,他坐在石頭臺階上,並沒有唱歌,在發呆。反而聽得見屋裡大家的吵鬧,筷子擊打桌面和聲嘶力竭的歌聲。
(總是忍不住寂寞掉下眼淚,
用最邋遢的樣子去面對,
迎接一次又一次心的破碎。)
唱走了調,這是誰,分明在乾嚎。他們還在猜拳。他聞到了一股香殊蘭的芳香。他思忖,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相信能夠做到。記得那一天好像是父親和他徒弟的生日。姜抱彈唱了《二流的把戲》、《回憶裡的那個人》。姜抱接連一口氣唱了十五首歌。有人喝醉了。
正在哭。
(簡直琢磨不透,你到底喜歡她哪點。
生活真的不容易。愛情更是荒唐。)
老羅家小兒子送定的炒菜來的時候,有個年輕警察正坐在汽艇上從河面經過,馬達聲音震耳欲聾,頭頂有七八隻信鴿掠過。水面漾起層層波紋,拍打著一塊夏天開彼岸花的礁石。
「好漂亮的花啊。」
「什麼聲音最動聽呢?」
「剛忙完,還餓著肚子。」
「都餓過了飯點。」
許多年後姜抱忘了當年修車廠誰最愛這樣嘟噥。肯定不是師兄弟,多半是客人。」
(彼岸花比血都紅。
你說的是床單上的血嗎?)
(老雞哪可能還會出血。
是她把你的x x整破了吧,火辣辣的痛不?
希望那時我們仍能喜歡對方。
相互攙扶。讓微笑永遠都縈繞心間。)
飯館的小老闆又懂個屁,聽他這樣連說帶唱,爛噪子,一個公鴨嗓子,都替他感到害臊,真恨不得一頭扎到河底去。別再裝巴斯克維爾的獵狗啦,你這樣是推理不下去的。我感到故事蹊蹺。莫非你想把幻想當真相去告密?怕是我精神出現了分裂。從沒人曉得。沒有哪種結論真正靠得住。
「別來裝鬼。」
「你滾蛋吧!」
(別讓我再看到你。
相互擁抱入睡。
所以我想你分分秒秒,甜蜜在夢裡。)
連自圓其說都困難,也許你躲到學校廁所裡自己打飛機玩更實在,別對隨便什麼人都糾纏。(就算我們無法走到最後,我也不會再有遺憾。就算我無法判斷,我的喜怒哀樂和你無關。)「公狗上了母狗,又關我屁事。」他在那輛追尾的川路車旁邊說,一個在哐哐哐敲打。姜抱懷抱吉他勾頭在想,這種舒服跟追尾可大不一樣,早遲要站灶臺邊的那傢伙,一個公鴨嗓子,可和你想的拿豬大腸……完全不是一回事兒,雯兒當時笑得前仰後合,她也接二連三說肯定感覺不同。(即然相遇不足以留下對方,那就把驕傲留到最後。)別唱了。(還是有一些過程無法忍受。酸甜苦辣,總靜悄悄在岔路口等候。)
就像聲稱見個鬼,單家橋,修車廠,有哪個又真的是見到過?
時間接近了傍晚。
「即然我真衝她發脾氣……我估計,她對我所說的那些也並不完全會是真話。」
「我用不著刻意去想那件事。」
「因為我知道,那樣幹,自然有理由。」
「我只是在不經意短暫瞬間出了身虛汗。」
「確實,會想起那種可怕畫面。」
有一部分是真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