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兔子的景點(踏入一份城市文藝地圖)
2023-06-22 19:47:24 2

2018年度人民文學獎揭曉 | 金宇澄《繁花》輸出英文日文版權 | 明珠美術館《陳丹燕在路上》展覽 | ......

......「圖畫書界奧斯卡」
對文藝青年旅者而言,
選擇一個目的地不是為了其他,
而是重走一份文學地圖,
聽見歷史現場的迴響。

在1999年由波蘭導演阿格涅絲卡·霍蘭拍攝的電影《心之全蝕》中,17歲的蘭波才華橫溢、風華正茂,在魏爾倫的帶領下進入巴黎文學圈,卻最終因其桀驁與不馴而遭到排擠。然而,在蘭波的體內存在著一股不滅的火焰,催促著他前往太陽所在的地方,他留下了許多我們至今掛在嘴邊的名句——「我要變成所有人」、「生活在別處」、「在心碎的黎明」、「無邊的愛自靈魂深處翻湧」。

同樣,取材自英國當代文學大師克里斯多福·伊舍伍德自傳小說的影片《克里斯多福及同黨》,記錄了克里斯多福從1929-1939十年間遊歷歐洲(尤其是德國)的見聞。
它們,都是絕佳的旅行指南。
在旅行中,我們都曾經歷過類似的時刻——闖進一名藝術家(包括用文字來作畫的人)曾經踏足的地方。每每看到豎立在公園中央的雕像,一條用名人命名的街道,或者一座用故居改造成的小博物館,都會令我們感到驚奇。但這並不該是我們意料之外的事。
觸摸著這些遺物,我們這些旅行者變成了信徒,會思考他人是如何成為他人,又是怎麼創造出那些作品的。我們會四處打量,並情不自禁地思索,這座小山和清晨的霧氣是否給過他一絲火花?這個地方對他來說是靈感源泉還是偶然路過?自1981年,解答這類問題成為「文學履途」最鮮明的任務,那時《紐約時報》把「文學履途」當作一個短期欄目來運作。它在接下來的多年間時不時地出現,直到成為一個完整的專欄。
這就是為何今天要推薦這本書的意義,這些文學旅者的文章,不僅滿足了一個文學愛好者的所有想像,更在於,那本身就是文學作品的自然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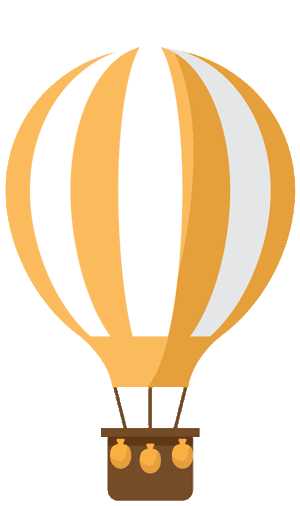
本書收錄了38篇與偉大作家有關的旅行地的遊記。風格各異的《紐約時報》專欄作者,用文字帶領我們探尋文學家在自然與城市中留下的「遺產」,以及他們創造出的那些不朽作品的源頭。
最早的一篇文章是關於莎士比亞的。
1860年刊登的一篇文章記錄了一次前往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Stratford-upon-Avon)拜訪「世界級的天才大師」莎士比亞的出生地和墓地的旅行。報導忠實地記錄了這個世界聞名的天才作家曾經留下的足跡:「周圍的環境靜謐,安寧,無比美麗。我想,那個曾在這裡度過童年的人應該汲取了這周遭的特質,變得溫柔、善良、充滿愛意,這一點兒也不奇怪。」這篇古老的文章便是「文學履途」系列的早期樣態,探尋了一個作家的身份、作品與其周遭環境之間的關係。

之後的一系列作品涉獵廣泛,每篇文章寫作的切入點也和那些文學巨匠各自的風格一般多樣。例如「馬克•吐溫的夏威夷」這篇文章,作者仔細查閱了馬克•吐溫在夏威夷島上居住的4個月中寄出的信,而不是回溯馬克•吐溫的小說。「奧爾罕•帕慕克的伊斯坦堡」則是另一種風格,讓這位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作導遊,帶領我們穿行於這個他住了60年的城市,他稱其為故鄉。
而《文學履途》書中描繪的歐洲是這樣的。查理·洛維特在牛津旅行途中,尋找愛麗絲的奇妙世界。英國作家劉易斯·卡羅爾,於1864年,在牛津遇見愛麗絲。有一個小女孩掉進了兔子洞,正在一個奇妙世界中,經歷奇妙的探險的故事。而這個故事後來便編寫成膾炙人口的《愛麗絲夢遊仙境》。

又如,大衛·謝夫特在《英格蘭海岸,託馬斯·哈代創造了自己的世界》這篇遊記寫到託馬斯·哈代,他於1874年創作小說《遠離塵囂》這部作品講述的是維多利亞時代一位獨立堅強的女生和她的追求者們的故事。而大衛·謝夫特在英格蘭海岸旅行中想到小說裡:「那個花心的軍官特洛伊正在英國南部的魯爾文海灣遊泳。」

大衛·拉斯金在《在彼得聖堡,過去的詩人是此刻的嚮導》這篇遊記中談到文學巨匠普希金。他在我們的眼裡完全比不上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的名氣大。
但是,俄羅斯人對普希金是狂熱崇拜的。在公共廣場、博物館、角落的海報裡,我們都能看到普希金。彼得聖堡的瘋狂,是以普希金的《黑桃皇后》為開端。普希金筆下的文字是無人可替代的。

大衛·拉斯金這篇「文學履途」正是今天要重點推薦的閱讀——
過去的詩人是此刻的嚮導

優雅的文學咖啡館就坐落於聖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在它的入口處,亞歷山大·普希金獨自坐在一張臨窗的桌前。樓上是餐廳,莫扎特的小奏鳴曲伴著瓷杯碰撞的叮噹聲,但普希金沒有在聽。他衣著完美,定定地凝視著空氣,這位詩人——至少他的蠟像是這樣——正在思索著愛情的苦澀秘密和復仇的甜蜜結局。
每一個能識字的俄羅斯人都知道,這尊有著濃密的黑色鬈髮和浪漫鬢角的精美蠟像就放置在一家咖啡館的窗口,位於喧囂的涅瓦大街旁,與肯德基相比鄰。那是因為1937年,普希金正是在這家咖啡店享用了他人生的最後一餐,隨後奔赴決鬥。

隨便問一個在此享用蛋糕的人,你就能聽到所有的故事:普希金向憲兵隊軍官丹特士發出決鬥挑戰,後者一直在無所顧忌地追求普希金的美麗妻子娜塔莉亞。那個傲慢的法國人先開了槍,擊中了詩人的腹部;這位文學巨匠在受傷後,痛苦掙扎了整整兩天才死去,年僅38歲。講故事的人甚至可能會抬起眼睛,驕傲地挺起胸膛,為你背誦一首十四行詩,或者長篇詩體小說《歐根·奧涅金》中的幾行詩句。
對於一個美國人來說,可能有點難以理解俄羅斯人對於普希金的狂熱崇拜。儘管我曾專門前往聖彼得堡,參觀和普希金相關的神聖之地——夏宮茂密的椴樹大道,年輕的歐根·奧涅金曾在這裡和他的法語家教散步,還有大理石宮的舞廳,這位百無聊賴的帥哥曾在此與聖彼得堡上流社會精英跳過瑪祖卡,但我還是被俄羅斯的普希金狂熱的範圍之廣、熱情之甚深深地震撼了。託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這些人在美國本土的知名度和接受度都比普希金要廣得多,但他們在自己的祖國被紀念的方式只有偶爾的遊覽線路和標識牌。而普希金無處不在,在曾經的首都聖彼得堡更是如此。在公共廣場、博物館、街角的海報上,到處都能看到他的形象。儘管這座城市經歷過革命和圍城,但是這名詩人的公寓,他上學時住過的宿舍,甚至他中彈倒下去的那一小片土地,都被精心保存了起來。

如果看背景,他真的是最不可能成為英雄的那個人。他是一個貧窮的貴族,其貴族身份承襲於曾祖父——一名來自非洲的奴隸;他是一位藝術家,融合了莫扎特的優雅和拜倫的諷刺辛辣;他是一名政治反叛分子,沉迷於狂歡和決鬥。但當第一首詩發表後,他就成了巨星。打個比方說,在他葬禮的那天,從全城各處而來的哀悼者只需要跳上計程車大喊一聲「去普希金那兒」,司機就能立刻腳踩油門把乘客送到普希金的遺體所陳放的教堂——他的名氣就有這麼大。在俄羅斯,把莎士比亞、託馬斯·傑弗遜和鮑勃·迪倫幾個人的名氣加在一起,那就是普希金。

「在俄國文學中,莫斯科是一個冷靜的城市——而所有的壞事都發生在聖彼得堡。」哥倫比亞大學斯拉夫語教授弗蘭克·J.米勒這樣對我說,「聖彼得堡的瘋狂,是以普希金的《黑桃皇后》為開端的。」故事的冷血主人公格爾曼,沉迷於追求一個賭博必勝的秘密而失了心智,事實上,在這座屬於普希金的瘋狂城市裡,幾乎所有的居民都在日以繼夜地偷情、飲酒、決鬥、狂歡、看戲,然後負債纍纍。普希金在《歐根·奧涅金》中表達過:「通達的人,我們承認,也能夠想法子使他的指甲美麗。」他用了五節詩來描寫主人公「換上夜禮服」的場景:

你可以說,他是個紈絝少年。
每天至少三個小時,
他要消磨在鏡臺前面,
一切完畢,這才走出梳妝室,
好像是維納斯出現在人間!
你看這女神穿上了男裝
翩翩地來到化裝舞會上。
以前曾有詩人將如此無聊的場景寫得這麼有趣嗎?通過香檳氣泡和法國香水,普希金構建出貴族生活的舞臺,他筆下的劇院與皇宮、飯店與舞廳,至今依然震撼地保留著原貌。果戈理或託爾斯泰的作品會描繪詳細可辨識的街道與建築,但普希金則更喜歡讓城市風景從疾馳的馬車窗戶裡一閃而過。誰也不知道奧涅金僱了馬車趕赴下一場舞會時走的是哪條街巷,也沒人會在乎:

風馳電掣地向那裡奔去。
在沉睡的街心,不少車成列
馳過一排排黝黑的樓房,
車前的兩盞燈射到飛雪,
閃著愉快的、長虹似的光芒。
前面顯出簇簇的燈火
照出了門廊,輝煌奪目,
和一座雄偉的巨廈的輪廓。
不過某一個晚上,在北方夏日的暮色餘韻中,我確實跟著普希金筆下那位鍾情於宴飲享樂的男主人公的腳步,來到了涅瓦河河畔的花崗巖河堤上。他曾在這裡聽著百萬大街上不絕於耳的馬蹄聲,「陷入沉思」。在這條大街上,從冬宮一直延伸到戰神廣場的位置,列滿了一棟棟百萬富翁的豪宅。我靠著同樣的花崗巖河堤,望著細雨在河上打出的朵朵漣漪。這條河在這一段與哈得孫河差不多寬,兩側河岸排列著狹長、低矮的皇家建築。好像事先安排好似的,當我俯身穿過那道橫跨在冬運河之上的拱門時,一匹馬正快步穿過百萬大街。冬運河是一條極美的運河,它流經冬宮側翼如峽谷一般的石頭建築——這裡又被稱作「大艾爾米塔什」或「艾爾米塔什劇院」。

天色終於全部暗了下來,我來到了彼得大帝騎馬塑像前,普希金在一篇敘事長詩中將這座塑像稱為「青銅騎士」。《青銅騎士》開篇描寫了彼得大帝劍指歐洲的磅礴氣勢——「我愛你,彼得興建的城/我愛你,嚴肅整齊的面容」,但是詩篇結束時,卻淪落至消沉與瘋狂。在之後,主人公的愛人死於1824年11月7日涅瓦河的洪水肆虐,他陷入瘋狂,總覺得那位「可怕的君主」騎著快馬,從那塊波濤般的花崗巖基座上一躍而下,在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追趕著他。
在探射燈的強光和夜晚花朵的濃鬱芬芳中,這座建於18世紀的青銅像以及它的石頭基座確實讓人感覺有點恐怖。普希金曾在詩中這樣描寫聖彼得堡:「壯美之城,乞丐之城/奴隸的氛圍,燦爛的面容/你的天堂擁有淺綠色的拱門/還有無聊,冰冷,花崗巖的優雅。」關於這座城市,他所鍾愛與厭惡的一切——美景與專制,壯麗與單調,優雅與冰冷,都在專橫的沙皇的凝視之下,度過了三百年。

普希金故居博物館位於莫伊卡河河堤旁,從冬宮過來只需要走五分鐘,這裡是所有關於普希金的地方中最神聖的所在。走過令人眼花繚亂的宮殿廣場後,沿著莫伊卡河的城市風景讓人感覺有種親密的孤獨——阿姆斯特丹的氣勢,威尼斯的微光,所有這些,都籠罩在聖彼得堡如水的北極光下。這是典型的普希金,他選擇在這座城市最美的水道上的最美的河灣旁居住,然而對於來到此地的普希金朝聖者們來說,這裡的優雅氣氛被詩人臨終那幾日所受的痛苦蒙上了陰影。
普希金是一個不諳世事又憤世嫉俗的人(他曾說自己的妻子是「我的第113位戀人」),對於別人的挑釁,普希金會極端敏感。1836年11月4日,當他收到那封匿名信,信中將他推舉為「綠帽子協會副會長」,諷刺他的妻子與丹特士公開調情,他嫉妒得發狂。在故居博物館入口旁的房間裡,陳列著娜塔莉亞小巧的粉紅色舞鞋,還有普希金決鬥用的那把手槍,它們被放置在天鵝絨鑲邊的盒子裡,好像聖誕節的裝飾——詩人的悲劇像是一首實體化的俳句,這樣擺在你面前。
鄰著莫伊卡河的套房是如此莊嚴寧靜,任何一位文學大家都會夢想擁有這樣的房間——高高的天花板和窗戶,紅色與金色的地毯,鑲金邊的燈,紅寶石般的酒瓶。但對我來說,在他工作和去世的房間裡,他的形象變得實在了起來。書房的牆壁上擺著約四千本藏書,棕色和金色的皮革書皮呈波狀起伏,他寶貴的手杖和土耳其佩劍就近在眼前,從三扇面向庭院的窗戶中透進來的光輕柔地灑在桌子上,照著那些留下的紙、書籍還有小玩意兒。
書架下方的陰影籠罩著那隻沉重的胡桃木包邊沙發,詩人就躺在這張沙發上死去,做著攀爬書籍的夢。


![]()
2019午夜藍文學周曆 x 詩歌主題周邊 已上線

最迷人的午夜藍,
是親手撕下的文藝時刻。

文學照亮生活
公號:iwenxuebao
網站:wxb.whb.cn
郵發:3-22
掃描左邊可進入微店
文學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