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西粟姓起源(全州姓氏溯源7粟丹東)
2023-10-13 00:28:16 4
廣西粟姓起源?粟丹東看到這個標題,心裡就感到有些沉重,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於廣西粟姓起源?下面內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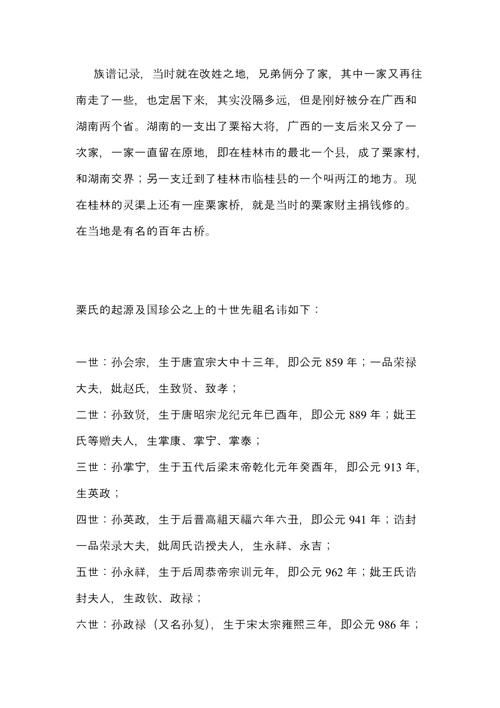
廣西粟姓起源
粟丹東
看到這個標題,心裡就感到有些沉重。
20多年前的1997年,筆者應桂林《灕江日報》李肇隆總編約稿,未作認真考查,只憑長輩口傳寫了《粟姓的由來》刊發在報紙《姓氏探源》首篇裡。文中,筆者介紹了粟姓是由熊姓改姓而來。現在回看,發現有些差錯,個別地方甚至存在表述錯誤。
2018年,全國粟氏在湖南粟裕大將的故鄉——會同召開了第一屆聯誼會,從會上公布的調查資料顯示,目前全國粟氏分別有稱由熊、孫、米、宿等改姓,也有說是古老姓氏,說法各異。而這些說法,有的只是傳說,但缺少真憑實據;有的則是瞎想,無根無據;各地所奉始祖分別有萬成、國珍、富國、實寰、傳昭等諸公。其粟氏後裔主要分布在廣西、湖南、貴州、雲南、四川、陝西和湖北等地,全國粟姓總人口不足30萬,姓氏排名靠後,近300位。單從姓氏人口來看,個人認為粟姓非古老姓氏,應是一個新生派年輕姓氏,易姓而來的可能性極大。通觀全國粟氏所奉始祖,惟資源縣粟萬成為最老,五代人。其餘諸公出生時間皆晚於北宋。
資源縣萬成公之源流
資源縣《粟氏族譜》共有12卷,成書於1928年。由於當時通訊和經濟條件的局限,合修這本族譜的粟姓,僅是資源、全州、興安三縣的萬成公後裔(1993年重修時,增加了湖南邵陽縣及靈川定江鎮的粟姓)。
這本族譜雖然刊印較晚,但它是在各分支的草譜基礎上彙編而成,各分支的世襲基本清楚。在族譜第一卷引用萬成公墓志銘對「一世祖」粟萬成作了這樣的注釋:「公生於五季(代)開平四年(公元910年)庚午三月初三日午時,原籍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於高祖時以武功拜御史中丞封為白公郎,因忤權要解組避隱,始遷於粵之西延泉塘坊居焉,『原姓熊氏易姓曰粟,此我粟氏之由來也』。享壽八十有三,歿於宋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壬辰八月十五日申時,葬西嶺崩衝椅形壬山丙向,碑載附會可疑之處未錄。」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墨譜序中也對萬成公的源流作了同樣注說「…解印避隱始遷粵之清湘西延泉塘坊居焉,舊屬軒轅玉牒氏,因遭兵戒易姓為粟,為江陵粟氏之」。
除了在《粟氏族譜》中對萬成公易姓為粟作了注說,還在萬成公後裔中有這樣的傳說:當年萬成公帶著一家逃命沿湘江逆流而上,在今天全州縣與興安縣交界的界首時,遠觀西邊越城嶺山高林密適合隱居,便棄船改走山道(1934年12月紅軍北上一軍團和中央縱隊的行軍路線),當走到資源「三斤界」回望來路時,仍見一隊荷帶兵器的殺手從對面山道尾追而來。萬成公與妻兒連忙隱匿於路旁長得十分茂盛的粟地,並許下諾言:「粟子,粟子,你若保護我躲過這場殺身之禍,我將隨你姓粟。」追兵一會追至粟地,下馬問山上種粟山民可曾見有人路過。種粟山民如實答道:「有,已過三斤界。」因地方方言與官話發音差異較大,追兵誤將「三斤界」聽成了「三千界」。追兵本已人困馬乏,望了望重重山巒、條條山脊,感嘆山道遙遙,只好鬱郁而返。萬成公與妻兒藏在粟地,追兵與山民對話句句聽得真切。待追兵遠離後,萬成與妻兒方才走出粟地,善意的山民賜予粟子粑粑充飢。謝過種粟山民,萬成一家劫後逢生,下山落籍於山環水繞的西延泉塘坊(今資源中鋒鎮官田村)易熊為粟。萬成公一家辛勤躬耕,以德治家,不久便成為村中人丁興旺且有威望之家族。
這個傳說,在資源、興安、全州、灌陽以至外遷湘川黔陝的萬成後裔中都是大同小異的說法,既使就是在全州和資源的熊姓中,一般人也知曉粟姓是由熊姓改姓而來。
筆者2019年9月在貴州三穗全國粟氏代表大會上作專題發言後,個別支系的代表直接發問:「粟子是北方糧食作物,資源種過粟子嗎?」以前也有人在家族群裡或是打電話向筆者提過同樣的疑問。資源種過粟子這是肯定的。筆者在上世紀60年代末也親眼見過。《資源縣誌》(1998版第247頁)記載:「1990年全縣糧食產植佔種植業的88%。糧食作物以水稻為主,玉米、薯、豆、粟次之。」
全州、資源和興安的粟氏由熊改姓,一代代如此傳說,族譜也這樣記載。經族譜統計,粟氏一世至今已歷39世,時間為1113年,若每代按平均27歲計算,從一世到39世時間近1100年,代際差沒有問題。
單說全州的粟姓,大都是明清時期從資源粟家大坪遷入,因粟家大坪位於寶鼎嶺下,翻過寶鼎嶺就到了全州。全州大西江魯塘村和勝田村的粟姓遷入時間較早,為元朝(約公元1350年左右)遷入,現在兩村粟姓人口超過1000人;而才灣鎮從粟家大坪遷入的主要分布在山川的「三灣」,既紫嶺村委的粟家灣、驛馬村委的信家灣、五福村委的桐梓灣(修五福水庫淹沒後分別搬遷五福和新村村委)。此外,在鹹水鎮的洛江村委和焦川村委,也有一部分從資源粟家大坪和上梁遷入的粟姓;石塘鎮的馬鞍嶺和焦江也有部分粟姓,但這部分粟姓何年由何地遷入目前尚未弄明白。
全州粟氏在科舉時代未出個有名望的人物,縣誌和家譜上僅見兩例:一是大西江魯塘村的粟大綱,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甲午科中武舉,據說後來率兵外地剿匪未歸;二是才灣信家灣的粟良弼,從九品。在全州做過官且《全州志》(康熙已巳年編九十三頁)有記載的是第20世粟林,原名士林(灌陽人),生於明洪治七年(1494年),授全州典史(知縣下面掌管緝捕、監獄的屬官)。
柳開招安資源粟氏
查閱《全州縣誌》,了解到全州在宋朝988年時,從北方來了一位叫柳開的知州。《宋史,柳開傳》記載: 「徙全州。全西溪洞有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開為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辯者得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即有厚賞,給田為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民懼,留二吏為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偕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如期攜老幼悉至。開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譯文:後來柳開調任全州。全州西面的溪洞有一個粟氏家族,聚族五百多人,經常抄掠人口、糧食和牲畜。柳開為他們做衣服、帶子和帽子,又挑選手下官吏武勇和善言辭的三個人,派他們到粟氏家族告訴他們說:「你們能夠歸附我,就可以得到厚賞.給田和修建房屋來安置你們。不然的話,就發兵深入你們村,把你們消滅掉。」粟氏家族非常害怕.就留下兩個官吏做人質,粟氏的首領親自率領四個酋長與另外一個官吏一起來見柳開。柳開給他們優厚的賞賜,官吏和老百姓都爭著以鼓樂歡迎他們,以酒食款待他們。柳開把他們留著住了幾日才送他們回去。他們按期把全族男女老幼都帶了來。柳開就為他們安排好田地和居室,並做《時鑑》一篇,刻在石碑上以告誡他們。又派他們的首領入朝,委任他為本州的上佐。柳開也因處理這件事情有功.皇帝賞錢三十萬)。柳開到全州任知州,為什麼對「為匪作亂」的粟氏不進剿而是招安?原因是,他的前幾任對溪峒(資源)被逼上山為「匪」的粟氏差兵圍剿,可是山高林密,「眾匪」神出鬼沒,不但剿不滅,反而越剿越亂,越剿越兇,其勢危及廣西省府(桂林)。柳開多謀,反其道而行之,改進剿為招安。粟氏被招安以後,溪垌就由湘西三不管地區成了全州的「西延」區,歸入了全州管轄版圖。這樣,一直沿襲到解放後西延才劃為資源縣。
史料還記載,當時招安設了指揮所兩處:一處為官田,一處為官垌(現今這兩處分別是官田村委和龍溪村委),兩處皆為粟姓主要居住地。989年招安成功,當時二世粟貴振正值盛年(生於五代乾佑元年即公元948年,葬西延八方小脂有碑,墓誌和族譜皆記有「因平亂有功,封為八十二郎),其不但進京見了皇帝得了賞賜,還封本州上佐官。柳開也因招安有功次年得以晉升,另外還得了30萬賞錢。柳開用這筆賞錢在全州北山置辦了書院,還親自到書院講學。後來,人們為紀念柳開開化全州的功績,將北山書院署名為「柳山書院」。
宋史記載,當時可能是「惜墨如金」的緣故,文中「粟氏聚族500人槍」 沒有過多文字交代。這裡的「聚族」究竟是指溪峒(代指資源縣)少數民族,還是指粟氏一族之人?給人留下猜想的空間。敞若「粟氏聚族500人槍」是指聚集少數民族500人槍,這只是以粟氏為首而已,那資源《粟氏族譜》記載由熊易粟,粟萬成被奉為一世始祖就沒有問題;敞若「粟氏聚族500人槍」指的是聚集本家族500人槍,那粟姓由熊易粟,一世始祖就並非是粟萬成,而是另有其人,易姓史就必須得再往前推幾百年。因為粟萬成出生到柳開招安還不到100年,全部族人加在一起不足300人,到哪去找能舞槍弄棒「為匪作亂」的500族人呢?
至於「始祖」粟萬成是否做過朝庭大員,既「於高祖時以武功拜御史中丞封為白公郎」,今人無從查考。猜測是在被柳開招安以後,其後人有意拔高祖上曾經「輝煌」過。假若真是於高祖時以武功拜御史中丞封為白公郎」,那就要遠溯到楚國熊姓王族某位高祖時代,這就像是一個猜不透的謎,難以考證。
眾所周知「地以人而名」這個道理,資源在唐朝前無史可溯。《資源縣誌》記載「會昌年間(公元841-846年)外地人到寶鼎朝佛,有部分人在資源定居」;「乾符年間(公元874-879年又有許多避兵禍(黃巢起義)的人到西延定居,此後,漢苗瑤各族雜居,推有威望的人為頭目)」。另據資料統計,「西延單姓人口較多的是唐、李、劉、莫、王、粟、楊、藍」,再從粟氏始祖佔居資江江西河谷開闊之地「官田」和「官垌」來分析,粟姓應當是到資源定居較早的姓氏之一,並非萬成公五代落籍於「溪峒」易熊為粟,粟氏易姓時間應為更早才是。因為只有在一地成為旺族,才有資格被推舉為眾族之首。也就是說粟貴振被推為眾族之首時,家族已走向繁盛。若此結論成立,那資源《粟氏族譜》只是家族中的斷代史,家譜所記載的僅是招安由「匪」成為「良民」的族史。故,粟貴振的墓誌和族譜裡就避諱了「招安」二字,只記為「平亂有功」。
資源萬成公、湖南邵陽仲庫公、靈川定江奉鑾公三支合譜緣由
1993年,廣西資源萬成公、湖南邵陽仲庫公、靈川定江奉鑾公3支後裔合修《粟氏族譜》,緣由如下:
湖南邵陽仲庫公後裔經考族譜,譜中曾有注釋,相傳粟姓與熊同宗,另見宗親馥公又抄錄有全州譜序記載有遷往邵陽之宗親,仲庫公與萬成公相差近二十餘代,且仲庫公的出生年代與萬成公後裔「仲」字輩年代相同,外遷可信。
靈川定江鎮粟家村原本有部分宗親民國就與萬成公支系合譜,但所剩大部祖源一直不明,分析附近九屋所立「有弘公」、臨桂所立「國珍公」發展只在800年左右,皆晚於資源「萬成公」,原本村分支與資源合譜符合情理。
於是資源、邵陽、靈川三方便求同存異,達成合譜協議。為解開萬成公《粟氏族譜》記有宗親遷湖南寶慶(邵陽)、靈川之迷,三方宗親代表又特於1993年清明節,登上資源縣楓木西嶺萬成公墓地開墓堪碑(迄今墓地共立有4塊碑),當時墓地是3塊碑。第一塊立於封土外正前方;第二塊和第一塊被掩於封土之中。墓碑乃前人為之。當第二塊立於光緒年的石碑呈於異鄉宗親面前,只見墓誌與族譜所錄文字毫無差異,宗親們疑問盡釋。筆者也曾親眼見證,當時資源宗親問靈川和湖南邵陽宗親是否有必要再看最裡邊的第一塊墓碑?大家都說,「明了明了,不用再看了」。於是便促成了三方合修族譜的良好局面。目前邵陽粟姓人口達20000多人,佔全國粟姓總人口的十分之一。邵陽杉木橋鄉的粟家祠堂,初建於光緒八年,規模極為宏大,佔地面積達4800平方米,在全國粟氏祠堂中當數第一。資源官田祖居地的家祠家廟因修建歷史久遠,盡被毀壞,現只有遺址。值得一提的是,資源龍溪粟氏祠堂雖然不大,但紅軍長徵時進村住過,還有幾位落伍的傷員在祠堂裡躲藏療傷,現已修揖一新,掛牌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成為當地紅色教育基地之一。
萬成公後裔遷徙到了哪些地方?
縱觀《粟氏族譜》12卷,從中發現舊時外遷宗親主要有五大因素,按照對家族影響大小程度來區分,個人觀點依次是:移民、任職、逃難、經商和從軍。其實,在族譜中先輩對此也作了定義,「主要是行商與遊官」。只不過這定義不太全面而已。
移民。眾所周知,我國有史可考的幾次大移民,其中明末清初的「湖廣填四川」對湖廣行省影響較大,僅在資源族譜中清楚記載的就有幾十人之多。這些外遷的宗親後來又影響著在窮山惡水中艱難生存的族人。他們又在不同年代引領一些族人帶著對美好生活的嚮往、離開故土舍家出外謀生和發展。由於各種條件限制,又經過幾百年的社會演變,這些外遷宗親的後裔基本不知根在何方。
任職。這就是先輩們所講的遊官。獲得功名到外任職是光宗耀祖之事,特別是寒門走出去的官員哪怕是七品芝麻官也是為整個家族大長家風大撐門面的事。因此,這些走出去的官員不分職務高低,自己的下一代便自然而然將異鄉為家。另外他們還關注著有外出意向且有發展潛力的族人,不吝伸出援手幫助他們離開故土外遷立業。舉例為證(儘管這些任職先輩所在地宗親目前尚未認同和對接):貴振公第24代的「粟應惠(字若蘭)系清太學生(《全州縣誌》有載),他的出生離現在已是300餘年,雖然他任何職在何方現在無法考證,但他的成功影響了下一輩,他的1個兒子歿葬失考、他的侄子「於瑞(生於康熙十四年即1676年)就是走出去的典型,譜載於端死後安葬在思恩府(今廣西平果縣舊城)。於瑞的兩個弟弟於謨、於規也一同在南國開拓立業,兄弟三人的後裔也從此失考。
又如27世良倬,名廷(珽)字少蘇(邑庠生,生於道光元年即1821年),他以府學第一的成績到順天府(明清兩朝北京地區稱為順天府)從事府尹一職,他的兒子尚通就成了失考人員,良倬兄弟三人都是例授官員,前後5世平均每代有兩位例授官員,他的侄子仕選作為六品軍職分發到廣東巡政廳任職,一家人每代都有失考人員,這些失考人員去了哪裡?不容置疑就是因為父輩作為遊官而隨遷異地。還有30世的官現(邑庠生,又名官宴)任廣東訓導,他與妻子李氏生歿葬皆失考;又比如國錩(字能仁,生於1822年),投筆從軍精忠報國世守八品,歿於1855年,葬於情(靖)州府(湖南)。國錩一家幾代為八品官員,他年紀輕輕就死在任上,魂歸他鄉。
此外,又如權公26世孫千榮為清馳贈修職郎任職巡政廳(胞兄千鍾生於康熙1686年),也可能由於他異地任職,帶走胞兄千鐻和堂兄弟千鎰、千監、千奇、千釜,此等人全部失考;還有34世昌茂恩授九品(生於道光四年1824年),也是由於任職,他的長子懋年(生於1856年)遷往平樂配葬失考、次子懋春(生於1862年)和三子懋繼(生於1874年)都歿葬失考,只有小兒子懋德(生於1870年)無嗣歿葬老家。還有廣西桂劇創始人之一粟文廷兄弟3人盡遷桂林府,傳藝雖不是做官,但可歸於任職一類。
上面這些例子是年代較近的,尚有文字可考。但還有的僅憑家譜和正史片言隻語無法說清,也只有假設了。比如我們第五世紹纘(生於宋天聖七年既公元1029年)在宋朝時就遷居四川順慶府廣安縣,那時候如果不是到四川任職,而是去做生意連想都不可想,關山萬裡東南西北都分不清。為啥說是去任職?因為自柳開到全州任知州平息西延粟氏之亂後,二世貴振作為起事首領被宋皇帝封為本州上佐官,於是便有了世襲例授官員。舊時有個規矩,不管是例授官員,還是通過科舉考取的功名,一律不許在本土為官。因此,五世紹纘去廣安任職就成為可能。另外,在宋時全州城東門還設有粟家營,這是粟姓屯兵之地。兵營扎在護城河湘江邊,擔負護城之責。為何如此?可能是考慮粟氏野蠻、剽悍、無畏,帶兵殺敵是最佳人選。所以,這樣一直延續到晚清還有粟氏宗親分發外地從事練兵的官員。至今粟家營只剩粟家渡,村中無一名粟氏。粟家營開拔到哪裡去了?留下懸念。我想,不是往北就是往南從湘江水路走了。
外遷人員尋根難的原因公析
1.外遷人員絕大部分是失考人員。為了方便外遷宗親查找祖源,筆者對家譜清朝之前32世列代按輩依次載錄下來,明確記載外遷的達數十人之多,可目前找到的十餘支人,只有湖南寧遠縣梅子窩村一支(全村現近200人)是有明確記載的,其他找回的譜上記的全是失考人員,這就是為什麼定義失考人員絕大部分是外遷人員的原因。如四川南充粟永輝一支,過川始祖必悅在19世上與筆者先祖必懷是胞兄弟,除必懷老大在資源老家,其餘3個兄弟譜上都是失考。再舉例四川大足季家鎮粟國良一支,順治年過川始祖永祥及父茂倫(孟倫)在我們族譜上是失考中的失考,因為族譜中根本就沒有他兩個的名字。粟國良親自到資源尋祖無功而返,因他家手抄本把「孟倫」寫成了「茂倫」,譜書中根本找不到名字,後來筆者讓他寫出父輩的兄弟名字才弄明白怎麼回事;再如遷四川南充後因參軍又過貴陽的粟宏一支,其過川始祖仕瓏在族譜上也記的是歿葬失考,等等數不勝數。
2.諧音字是外遷宗親尋根的最大障礙。2019年以來,筆者通過多方聯繫,先後找回四川營山、宜賓、西充、金堂、自貢、大足,大竹、貴陽、陝西、寧遠、灌陽等多支宗親,在對接過程中發現因地方方言與官話的差異,輩分使用諧音字是造成尋根的最大障礙。舉例如下:
一例,筆者與四川大足粟國良對接既順利又坎坷。他與朝政一行2017年前就親自到資源尋訪過祖源,也清楚過川老輩叫友常(應為友瑺),結果他把友瑺的兒子輩分「孟」字輩記成了「茂」字輩,加上過川上一輩「茂倫」資源老譜又沒記錄,折騰了好些時間。幸好他們記得遷川前資源的胞兄弟及侄子的名字。後來筆者叫他把歷代名字一一寫出來對照,才知道問題出在那。
二例,自貢粟成林一支,與筆者取得聯繫後,提供輩分用字「應於昌世登,中良時上國」,筆者一看,家族分支21-32世有「仁金榮應於,明忠良仕尚,國盛」用字,他們前後10個字輩諧音字就有3個,除了諧音還插入了3個不同輩分,又漏了1個輩分。當晚筆者與他聊了很久,並確定是一支人,指出了他的錯誤之處,但沒達成一致意見。成林也很用心,晚上睡在床上回想了很乆,又聯想到老父親對他的面授,第二天一早告訴其真相,原來是他們村裡編譜時憑記憶出的錯,多出的3個字輩為「於」(於)字輩的3個名字,他們還把湖北麻城這個移民中轉站記成了遷出地。真是好事多磨。
三例,大足的友山公,坪灘的友金公,祖上講跟友常公是兄弟,筆者對這3名字腦中有記憶,不看族譜就懂是二房用康公派下的宗親,再看族譜是遷川的堂兄弟後裔,非胞兄弟。友山應是友珊、友常應是友瑺、友金應是友經。友瑺後裔一直沿用通譜無疑義,友經、友珊後裔入川後新立了字輩,輩分用字自然就不相同了(目前已聯繫但未完全對接)。
四例,筆者在宗親對接中碰到另有3支將桂林府寫成「貴陵府」和「桂陵府」的,其中一支已完全對接,一支前兩代字輩一樣,且全州這個地名也在他們譜序中,也無疑議,剩下那一支字輩完全不一樣,年輕人不懂也沒想花時間去弄懂。
郡望、堂號和家族傳說是宗親尋根的便捷標誌
郡望和堂號是中國人進行尋根問祖時不可不先熟悉的一個概念。但何謂「郡望」、何謂「堂號」呢?簡言之,「郡」是指某地的建制名稱,「郡望」就是指當地望族。「郡望」也稱地望。而「堂號」就是某一同族人的共同徽號。「堂號」其本意是廳堂、居室的名稱,後來用來代表一個家族源流世系,區分族屬、支派的一個重要標記。如果郡望、堂號一樣的姓氏,其祖先為同一祖先無疑;如果郡望相同、堂號不同,也極有可能是同一祖先;如果郡望、堂號都不一樣,那極有可能就不是同一始祖。關於「郡望」與「堂號」這兩個詞語,值得強調的就是「郡望」與「堂號」的關係:郡望是高一級別的宗族尋根標誌,堂號是比郡望低一級的宗族標誌。郡望可以作堂號,但堂號卻大都不能用作郡望。
全州姓氏溯源1:大姓蔣氏 全州姓氏溯源4:黃帝後裔十二姓氏之一的滕姓 全州姓氏溯源2:北宋遷至全州的經姓 全州姓氏溯源3:開通湘桂走廊咽喉全州磐石腳的曹氏 全州姓氏溯源5:宋代從江西遷至廣西大蒜之鄉的鄭氏 全州姓氏溯源6:唐代兵部尚書德佑公的後裔倪姓 再辯蔣琬故裡究竟在哪?(四)《蔣氏受姓之地並吾宗所自出考》 全州蔣姓又多了一位百歲老人,蔣氏文化研究會正、副會長前往祝壽 請全州劉氏朋友看看,這支興安劉氏是否來自紹水石鼓劉家的劉氏? 全州蔣氏修繕三國蜀相蔣琬公祖妣毛氏一品夫人墓紀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