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歸真正的故鄉(正在消失的故鄉)
2023-07-25 04:56:04 1
回歸真正的故鄉? 我的故鄉在景泰縣城西北二十公裡之外的一個小山村,這裡三面環山,只有村子的東北方向敞開著,站在緊挨村莊西北的後大山上極目遠眺,遼闊的內蒙古阿拉善草原盡收眼底,現在小編就來說說關於回歸真正的故鄉?下面內容希望能幫助到你,我們來一起看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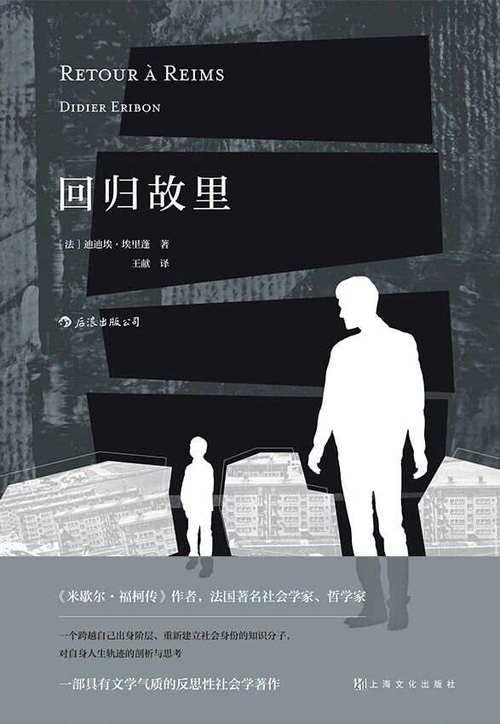
回歸真正的故鄉
我的故鄉在景泰縣城西北二十公裡之外的一個小山村,這裡三面環山,只有村子的東北方向敞開著,站在緊挨村莊西北的後大山上極目遠眺,遼闊的內蒙古阿拉善草原盡收眼底。
不大的村莊被一條沙溝分割成南北兩半。南岸地盤較小,稱做南臺,北岸佔地大一點,是一座古堡,村民們都習慣叫城裡。沙河兩邊是沉積了幾百年的陳灰堆積而成的堤岸,高有一丈有餘。
村子叫三眼井,的確,在城裡有三口水井。一口在村西北的後大山腳下,叫上馬泉,一口在城中心的戲臺的旁邊,叫中泉,一口在村子最東頭,叫下馬泉。上世紀七十年代,村裡將地勢較高的上馬泉用管道引至地勢稍低的村東頭成為泉水,至今汩汩流淌,晝夜不舍,供應著全村的人畜用水,並且形成一個澇壩,澆灌著附近的菜地和麥田。中泉被填平乾枯,下馬泉廢棄,但仍有泉湧出,廢而不棄。這裡泉水清冽甘甜,所以方圓幾十裡都有「一個巴掌打到三眼井喝涼水」的說法。
既然是古堡,肯定有一定的歷史傳承,翻閱史書果然有明確記載。據明史記錄,萬曆二十六年(公元1598年)兵部侍郎兼三邊總督李汶率軍在大、小松山(今甘肅景泰、天祝壽鹿山昌林山一帶)擊敗蒙古阿赤免和海部,將明朝國境線東擴400裡,李汶上書朝廷廢原來從靖遠過蘭州經永登天祝古浪到武威-千餘裡的舊長城,修築了一條從靖遠過黃河經索罕堡直達武威只有400裡的新長城,省時省力,這就是「松山新邊」。為了加強對新邊的支援和控制,新建鎮虜堡、蘆陽堡、三眼井堡、紅水堡,連接省城,後又增修永泰堡(公元1608年)。據時任兵備道副使荊州俊所著《三眼井堡記》記載,三眼井堡於萬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完工,規制和紅水堡相同。
明亡清興, 這裡失去了防禦作用,雖然久為內地,仍然有兵駐守。至遲在清順治時,三眼井設都司一員,屬於四品武官。根據乾隆年間修的《皋蘭縣誌》記載,三眼井有都司一員,把總一員,外委一員,馬戰兵十三名,守兵一百二十九名,在新邊諸堡中駐兵最多。這主要是因為年羹堯在平定青海後,建議以明邊為界,內地與青海諸部只可通市,不得互遷。因此,雖為一國,但在邊內邊外之間流動的人口,需要有通行證,得到批准,交納稅金後,方能遷徙。主要控制的是蒙古刺嘛到青海塔爾寺敬香,以及因蒙古各部之間的互動而引起的地方不安,所以這條道也叫喇嘛路。這在法國傳教士古察伯的《韃靼西行旅記中》有詳細的記錄。這個法國人裝作蒙古喇嘛從北京去西藏,沿途路過三眼井,並在這裡的驛站住了一晚,由於通關時,文件不全,遭受了邊兵敲詐,他對三眼井並沒有留下什麼好印象。估計他是有史料可靠的第一個到達三眼井的歐洲人。
除此之外,在清朝,三眼井也是一個驛站。按清實錄記載,應該是在雍正五年(1727年),在裁汰武威,古浪等九驛後,新設了三眼井驛、寬溝驛和營盤水驛。在三眼井的過客中,最有身份地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康熙的十四皇子胤禵,他在西徵的時候,路過並在三眼井住了一宿。在康熙五十八(公元1719年)年三月初五這天,這位西徵途中的皇子在寫給康熙帝的請安折中匯報到「二月十二日宿於三眼井地方,恭閱請安折內硃批諭旨」。另外一位是班禪額爾德尼貝丹益西即六世班禪,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的清實錄曾多次記載如何安排班禪喇嘛從西寧到三眼井的路線以及沿途驛站的料理事項,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六世班禪終於順利到達熱河朝謹乾隆皇帝。這個驛站一直延續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但作為稅卡一直存在到民國初年。
同治二年(公元1862年)以前,在三眼井這個彈丸之地,有人口一千餘,三百來戶。「先有申、尚、牛,後有顧、梁、侯」的說法,至今村裡大人小孩皆知,這不光是說這六姓是較早來三眼井的,而是說當時他們有一定的社會地位,是當地殷實之家,家境富裕,有實力購置田產,有很多田產地名,都是按其姓氏叫的,如申家灣、顧家溝、侯家窯、牛家莊子,於家窯、於家淌、王家莊子等,城內有王家巷子、申家園子、侯家園子,城外有餘家上園子、馬家園子、馬家街等等,這一切都是歷史的見證。
據老人口口相傳,當時堡內的王家巷、馬家街、餘家店鋪、雜攤小吃館、醫藥當鋪,客棧糧店,生意紅火;都司署、營務處人員進進出出,忙於辦理公務,;營盤臺子、教場灘,兵卒有序地操練;馬號梁上的馬號裡,馬夫牽馬備鞍,驛員背挎公文袋,準備往下一站交送文書。庶民百姓,春種秋收,安居樂業,軍民共處,其樂融融,在明末清初近兩百多年的歷史時期,也是三眼井興盛之時。
到了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陝甘回亂,寧夏金積堡新教(哲合忍耶)第五代教主馬化龍起兵反清,大肆屠殺漢人,他夥同從陝西西竄的回族叛匪馬士彥、楊文治部殺入紅水、三眼井一帶,攻陷三眼井堡,他們將堡內變成人間地獄。叛匪將躲在關帝廟的數百名村民盡數殺戮,大街小巷,人頭滾滾,血流成河。殺人之後,隨即一把大火,將鱗次櫛比的民宅和商鋪化為灰燼,大火經日不滅,以致於讓這個昔日繁榮的山村淪為名符其實的「灰堆」村,也為古城堡百年後的徹底消失埋下了伏筆。經此一劫,百姓逃亡,人口銳減至三分之一,城垣殘破。光緒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驛站撤銷,再加上民國戰亂,迭遭天災,三眼井便一厥不振,八十年間衰敗不堪。
一九四九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三眼井這個古老的山村也煥發了生機。經過休養生息,經濟逐漸復甦,尤其是到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口恢復到七百餘口,一百多戶,分成兩個生產隊,又聯合相鄰小營盤水和紅柳泉兩個村子,三村四隊,組建了三眼井大隊。各種公共設施也陸續建起來了,大隊部,供銷社,醫療衛生站,獸醫站,信用合作站,機磨房,戲臺等應有盡有。最讓人們高興的是在原來五年制小學的基礎上增加了初一初二兩個年級,成為「戴帽子初中」,讓三個村子的學生能夠就近上初中讀書,學校一度有十四、五名教師,學生達到二百多名,興盛一時,這裡也成為恢復高考後最初幾年產生大中專學生的搖籃。三個村的文藝調演,籃球、拔河、鞦韆等比賽也是搞得如火如荼。一派興欣向榮的景象,大有中興之勢。
然而好景不長,隨著自然環境的日趨惡劣和人口的增長,人與自然的矛盾日益加劇。五十年代初,古城堡除城門損壞外,其它四周城牆及角墩基本完好。但由於陝甘回亂造成城內全是深達二米到幾十公分不等的陳灰,無土做土坯(蓋房砌牆用的土塊),村民們只好挖城牆取土建房,就這樣一點一點地蠶食,最終變得千瘡百孔。文化革命時期將遍布村裡的十幾座廟宇當做「四舊」悉數拆毀。同時也隨著景泰電力提灌工程一、二期的陸續峻工,經過前後兩次的人口遷移,從八十年代初開始,這裡日漸沒落,終於在一九八九年隨著全體村民的整體搬遷成為無人居住的荒村了,而我也於一九八五年離開了故鄉。
如今的三眼井,古城堡只剩下殘垣斷壁,昔日高大的灰堆也因為能做肥料被附近景電灌區的村民拉的蕩然無存,若大的村子只有一戶牧羊人在這裡孤獨的守護著羊群,荒草野叢中野免、狐狸時常出沒期間,只有那汨汨的泉水還在不舍晝夜的流淌著,仿佛它還依稀記憶著這裡曾經的榮光。
這就是生我的故鄉,是哺育我十九年的故土,它陪我度過了一個美好而艱辛的青少年時代,就在它衰敗之時狠心的離開了它,而它也成為我永遠回不去了的故鄉!
寫到這裡本該結束此文,但忽然想到有兩點遺憾未能說到,一個遺憾是自始至終故鄉都未能留下一張完整的照片,使後人再也無法見到它的真容,它也必將隨著見證者的逝去而永遠消失在歷史的長河當中;另一個遺憾便是故鄉到最後消失時也沒能通上電,至亡它也沒能被現代文明的曙光所照耀,這不能不說是故鄉的悲哀了。
痛兮故鄉,永無相見,鳴呼哀哉!
謹以此文敬獻給正在消失的故鄉! (2022年12月23日晨)
,





![2022愛方向和生日是在[質量個性]中](http://img.xinsiji.cc/20220215/1604989894118215680.jpg)



